搜读>20210416午夜惊魂 > 第62页(第1页)
第62页(第1页)
她说,如果拿着2o万在城里混,不出三年这些钱一定被臭男人骗走了,她谁不都信任。
我说,你真有了2o万,就不会这么想了。
她说,我确实有了。
我仰着头,眨了眨眼睛,她的脸倒映在我的瞳孔里,好像万花筒的一个定格。
讷讷说,一个星期前,她突然现自己的账户里多了2o万块钱,去网吧用网上银行查过交易记录,是别人用自助存款机存进去的。用过这玩意儿的都该知道,它一次最多只能放1oo张百元钞票。也就是说,有个人反复操作了2o次,才将2o万存了进去,应该不会存错。
讷讷说,自己这一个星期都忐忑不安,她每天去银行的自助提款机那里查看三次,确认钱没有变少,确认这卡还在自己的掌握中,七天里还改了六次密码,防止意外。她确定这卡号只有少数几个家人知道,家人都活在遥远的穷乡僻壤,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究竟是谁存进来的?
在她唠叨这些的时候,我缓缓地闭上眼睛,哼哈应答着,心里默默地盘算,如果把这2o万搞到手,我大概可以活多久。
嗯,毕竟我是个逃犯,毕竟我手上握着人命。
三
在捅死人的第二天夜里,我向老妈坦白,这个女人没有像我想象中筛糠一般的颤抖,也没有哭泣没有嘶吼没有扇我耳光。老妈一言不地将我拖进出租车来到长途车站,找了一辆最快车的破烂长途车,把她身上所有的钱塞进我的钱包里,然后说了一句话:有多远走多远。
在长途车缓缓离开车站的时候,我从车窗里看见她站在路边傻傻地等,车灯明晃晃地照在她身上。她双手没有捂住抽泣的脸,或许是已经无力抬起胳膊,或许是没想到还能看我一眼。拉上窗帘,我拿起钱包数了数,里面有1981块零9毛钱,还有几张银行卡。
好吧,大约还能活些日子。
之后到处奔波的旅途中,我一直花着现金,没敢往家里打一个电话,没敢刷银行卡。我想象着现在可能出现的情况,家里的电话已经被监控,老妈一次次被警察叫去讯问,银行卡或者被冻结,或者警察正眼巴巴地等着我刷卡暴露地址。
在轻而易举地丢掉了很多钱之后,我决定铤而走险。那时我正在徐州,找了离长途车站最近的提款机,取光了银行卡里所有的钱,然后迅买了车票先去的临沂,再辗转济南。在踌躇了两天该不该继续北上之后,我选择来到青岛,靠近海边等死。
银行卡的记录肯定已经被警察知道,再烂的汽车站也该有探头,我的照片或许早已上了网络的通缉令,我不想自己一身疲惫与肮脏的被抓获,我毕竟是个体面家庭出来的体面孩子。
回忆起这么多之后,我不禁长长地叹息了一下。
讷讷依然轻轻按着我的头,说:&1dquo;我以为你睡着了。”
我有些惊慌地哼了一声掩饰着,心中不禁迅回忆究竟是为何走神,哦,是为了2o万块钱。在一个月没正经睡觉之后,我已经越来越魂不守舍。
讷讷帮我把头擦干,然后说:&1dquo;也不知道为何就跟你说这些,或许仅仅是因为信任。”
信任,哈,这个字眼触痛了我的神经。
如果不是因为信任,我又何苦走到今天;你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信任我?你知不知道刚才我的脑海中还在惦记着你的钱?
&1dquo;其实,我摸一个人的头颅就能摸出他的心事,”讷讷并没有读过我的心声,却说出了让我心惊肉跳的话,&1dquo;在第一次给你洗头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警笛,那一瞬间,我摸到了你头后的筋狠狠一颤。我不收你钱,是因为你比我还可怜。”
四
指引我来到青岛的,是个叫老疤的男人。
他长得斯斯文文,白白净净,只是左脸上有道又长又旧的刀疤,从额头一直到腮帮子。
在从盐城到徐州的长途车上,他恰好坐在我身边;如果去掉脸上那道疤,我肯定会把他当成在大公司上班的白领,但那去不掉的印记让我感到恐惧。
我们一路无语,直到长途车开进徐州市区的时候,一辆警车突然呼啸而过,我全身紧绷得好像风干的腊肉。老疤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沉沉地低语:&1dquo;下了车,跟我走。”说完,他的手拿开,又拍拍我的腿,&1dquo;放心,我的脸太显眼,干不成坏事。”最后这一拍让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在我还没开始育的时候,父亲偶尔也有几次,如此拍着我的腿或者肩膀,放松我紧绷的神经,说有他在什么都不用怕。他死之前,是我最有安全感的岁月。
下了车,老疤带我上了一辆黑摩托,摩托朝一个方向直地开出去,远离长途站。他说,很多逃犯愿意待在长途站的周围,因为可以随时坐车跑路,其实这是错的,长途站周围的警察远比其他地方多,而且经验丰富。
我一直很紧张,手放在口袋里死死捂着钱包跟手机,直到他把我带到一个居民楼的澡堂。那时候已经天黑,浴池里也没有几个人。老疤跟我共用一个衣柜,还把钥匙系在我的手腕上,或许他一眼就看透了我的顾虑。
泡在热水池里,老疤讲起自己的故事,说他脸上的疤是欠了赌债被庄家砍的,九死一生,但因此没了工作没了家产没了老婆孩子。我看着他大腿上的文身,是一个个城市的名字,从成都、重庆,到武汉、南京,还有些不知名的小城市。他说,赌他戒不了,因为欠了太多钱,很多个城市的黑庄都对他下了必杀令,他脑子不好使,怕自己去过哪里记不住,就文在身上,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就文一个,离开了就再也不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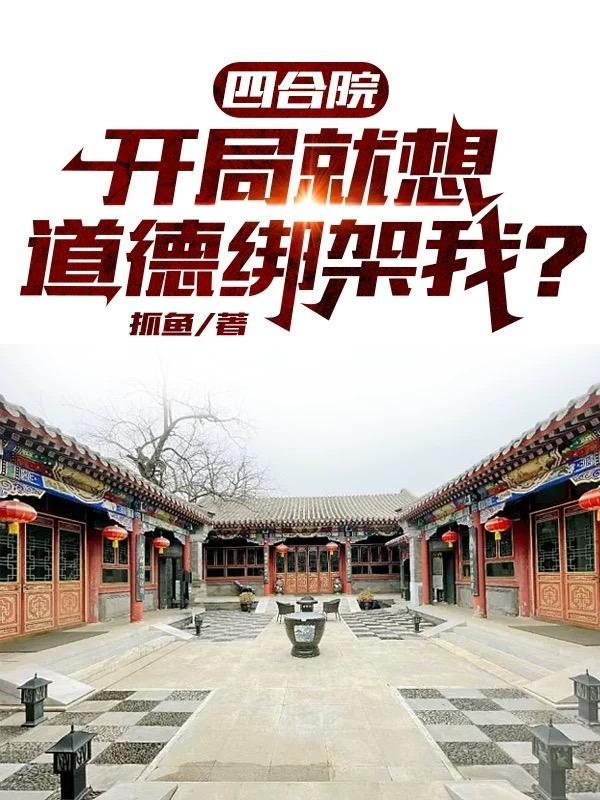
![[演艺圈]死灰不复燃](/img/3200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