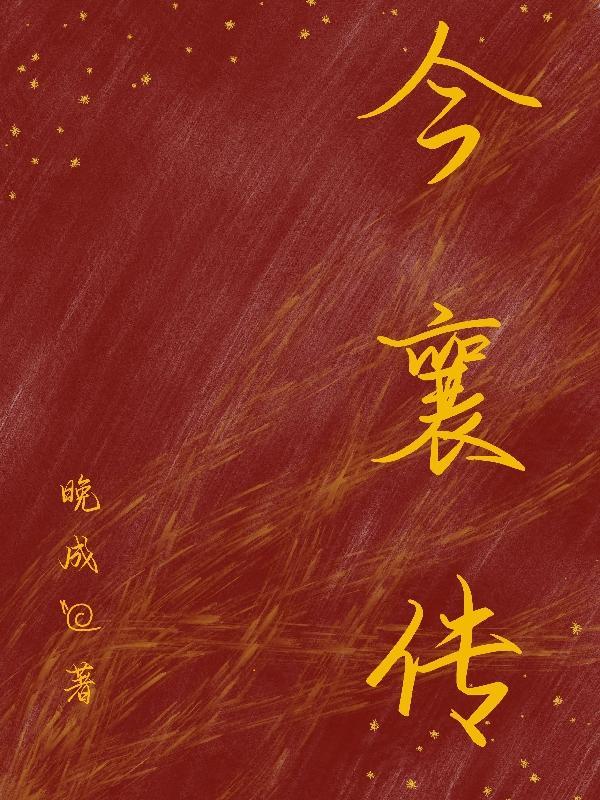搜读>雾夜新婚妄云栖全本完结 > 第五十章 紅甜橙(第1页)
第五十章 紅甜橙(第1页)
病房頂燈光線昏暗,照亮了來人的臉。
對方明艷漂亮,鼻與唇的形狀和柳拂嬿有些許相似。
但穿得叛逆不羈,一件玫粉色夾克配綠色的毛衣,襯得一張十分貴氣的面頰也很難得地透出幾分村氣。
薄韞白見她眼熟,想了半秒,才記起她叫魏瀾。
「我還以為薄家會把你嚴嚴實實地保護起來呢。」
魏瀾很自來熟地踏入病房,又揣著手看了看門外,用看熱鬧般的語氣道:「怎麼這門口一個人也沒有?」
薄霽明才走不久,而且薄韞白讓他先去布置柳拂嬿那邊的安保,保鏢應當是還沒有過來。
不過薄韞白自然不可能把實情告訴她。
他倚在床頭,雋冷麵容隱於光影之間,一對黑眸沉沉看不到底。
出於同是異鄉華人的緣故,薄韞白叫了一位整理圖書的志願者過去,給她指引方向。
「薄韞白,以你的身家,總不會不知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啊。」
「正事?」
薄韞白眸光一凝。
應該是不太熟悉圖書館的格局,所以才不知道哪裡有桌椅。
薄韞白掀眸看她,眸色漆沉。
薄韞白抬起眸,淡聲反問:「知道得這麼清楚,你也出過車禍?」
臉上好像都明晃晃地寫著一句話:「我是個扶不起來的敗家子」。
她笑意更深,譏諷意味濃得幾乎要從眼底漫出來:「你說,我哥是不是天選之子?」
在劍橋的圖書館。
沒想到,此刻的魏瀾卻在暗示他,敵人是魏坤。
然而魏家人的話不可盡信,他掀眸看一眼魏瀾,眸色仍漠然無波,淡哂道:「你爸現在活得很好。」
魏瀾沒看清他的動作,反而走近了幾步,低聲道:「車禍撞到頭,最好是別亂動。」
魏瀾說:「那你可別叫人過來啊。」
一個早已被淡忘的畫面閃過腦海。
薄韞白扯了扯唇,笑意不達眼底。
他還記得上次見魏瀾,對方一臉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模樣,橫衝直撞,無法無天。
「魏家三個兄妹,只有我哥毫髮無損。」
他微微支起身,將床頭柜上的一個東西握進了手心裡。
此時似笑非笑看她一眼,目光帶著幾分沉鬱,淡聲反問:「沒有麼?」
「先是我爸診斷出甲狀腺癌,兇險的很,遺囑都立好了。」
依稀記得,對方的目光清澈篤定,似乎並不是一雙溺於浮華的眼睛。
魏瀾一怔,還真被他給唬住了。
「結果前腳剛立好遺囑,後腳我哥就死於私人飛機失事,沒過幾天,我也車禍重傷。」
她說話的模樣寧靜而又條理清晰,乍看起來,和柳拂嬿的氣質有一點點相似。
不同於此時此刻,對方儘管穿得村氣,眉目間卻流露出一絲認真。
出於二十多年前的那場殺機,他最懷疑的人,原本是魏雲山。
薄韞白忽而憶起,沈清夜曾經問過他:「你們都在英國讀書,你有沒有見過魏瀾?」
她不確信地又看了看外面,開始疑神疑鬼,以為這是一出空城計。
「每天平躺,配合醫生按時做檢查,有些隱形的損傷,可能會延遲個幾天才能被查出來。」
那書很沉,但她看得很入迷,如獲至寶一般,雙手一直捧著。
「我找你有正事的。」
這句話並不怎麼客氣,但魏瀾竟然心平氣和地點點頭:「對啊,在我十二歲的時候。」
安靜的病房裡,薄韞白不動聲色地拼湊著記憶的殘片。
轉身之前,魏瀾帶著謝意看了他一眼。
她站在病床旁邊三四步的地方,不再走近,唇畔帶著一抹冷淡的笑意,像是講故事似的,隨口道:「那一年我們魏家可不太平。」
他之所以有印象,是因為魏瀾當時在看一本和飛機結構有關的大部頭教科書。
他確實見過魏瀾一次。
他現在對魏家的任何人都沒有絲毫信任,因為誰都有可能是指使方興寒的那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