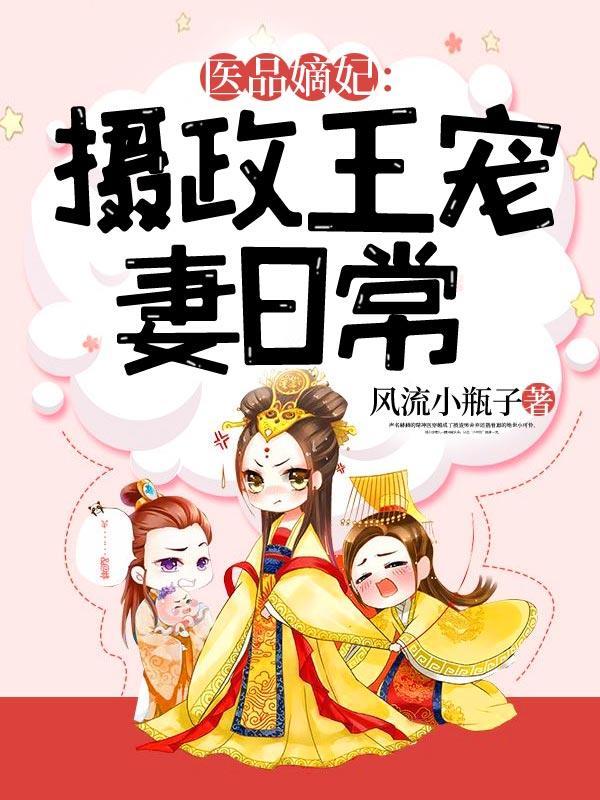搜读>失明后认错夫君全集免费 > 第64頁(第1页)
第64頁(第1页)
表面功夫誰不會做?
但她也知這對這婦人而言便是大恩,笑道:「您是好人,便也遇到了好人。」
婦人又夸那長公子有謫仙之姿、菩薩心腸,可阿姒一句都聽不進。
晏書珩見她沉默,心知無法僅憑隻言片語就讓她改觀。但他讓婦人和小郎君在露面,也不只是想讓她對他生出好感。
那小郎君很是乖巧。
見阿姒眼上蒙著布,稚聲稚氣地問:「阿姐是在和這位阿兄捉迷藏麼?」
孩子嗓音輕靈,阿姒柔聲道:「阿姐眼睛病了,這才要蒙眼。」
小孩明白了,安慰她:「他們說我身負祥瑞,我摸摸阿姐腦袋,阿姐就好了。」
阿姒溫柔地蹲下身:「那便多謝小郎君,說不定明日阿姐就能好。」
可小郎君驀地低落了:「阿父也被說是身帶祥瑞,從前我一摔倒,他摸一摸我腦袋我就真不疼了,可他卻未長命百歲。」
本應無憂無慮的四五歲孩童,卻流露出大人般哀傷。阿姒憐惜地摸了摸他的腦袋。
孩子年紀雖小,但甚是體貼,見阿姒看不見,又給她說起周邊景致:「兩岸林木蒼翠,崖上有飛流從天而降。」
阿姒認真地聽著。
婦人稱這孩子四歲,但他不僅透著早慧的靈氣,言辭亦有條理。
顯然出身自世家大族。
只是可惜了,如此聰慧卻早早歷經人世疾苦,她摸了摸小郎君發頂,晏書珩則安靜立在一旁,垂眼淺笑著。
小郎君回艙後,只剩他們夫妻。
晏書珩忽而問:「我記不清了,不知我可與夫人提過家中親眷?」
阿姒茫然:「你家中……啊不,咱們家親戚,夫君未曾提過。」
晏書珩放下心:「我雖寒微,但也算與晏家沾親帶故,也是知道晏家船隻要在武陵停留數日,才藉此機會尋訪故友。」
阿姒不敢相信,但想想也合理,若非與晏家沾親帶故,他又如何能替晏書珩做暗探,武功折損後又如何能在這個「上品必出自閥閱」的世道下在建康謀得差事?
她打消對船的困惑,嗔道:「此前為何隱瞞,憑白讓我起疑?」
晏書珩笑容更為溫柔。
依他對阿姒的了解,她即便起疑也只會在盤算後再暗暗試探。
但這次她卻直接問他。
他耐心道:「此前見你畏懼權貴,怕你不安,才不敢貿然相告,但阿姒放心,我非高門子弟,至親也只祖父一人,
「不過現在我的至親中,多了你。」
阿姒微頓,心中一動。
她恐怕也和他一樣沒幾個親人在世,可他這句話卻讓她久違地感到踏實。
這夜,他們照例同榻而臥。
這已然成了彼此都心照不宣的事,但此前他們各蓋各的被子。可今夜一上榻,青年便將阿姒捲入自己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