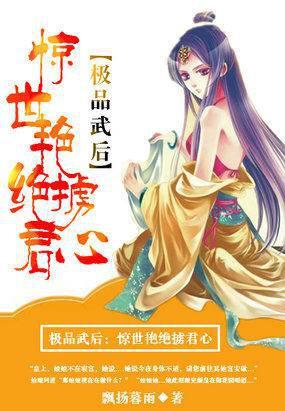搜读>直到日落在线阅读 > 第79章(第1页)
第79章(第1页)
沈时因一顿,险些说出那个字。她在脖子上做了一个“咔嚓”
的手势,“那再剩下的钱应该就是儿女分了。”
沈时因不由得想,他的一儿一女说不定会在心里日夜祈祷,希望自己的父亲早些离世,这样就能继承遗産。
“不止是这样,他们在调解过程中还签了一个协议。”
沈时因掰着手指说:“老头如果主动跟子女或者孙辈联系,那麽在电话里聊天是一小时五百,去养老院看望一次需要支付一千,节假日翻倍。从养老院接出去玩,也按时间算钱,一天两千。人人都讨厌他,但也都望着他手里卖房子的钱。如果哪天钱没了,人还活着,那可就真是人人喊打了。”
沈时因倒没有多同情这个601的前住户,她就是有些感慨,原来一套房子、一笔钱财就能让子孙后辈从人变成鬼。
这个解决方案整体还算圆满,钟琂问:“那你们现在的业主群在讨论什麽?”
“就是这二十万的分配。”
说起这事,沈时因叫苦不叠,“该怎麽分,大家都在争论不休。本来最开始说平分,但总有人有意见,说自己家里住的人少,水电费承担更多,就应该多分。还有人说要根据入住年限,近几年才搬过来的人应该少分一些,还有人说要请律师,律师费从赔偿款里扣,总之吵得不可开交。”
再照这样发展下去,好事也要变成坏事了。
沈时因本来只是在说明情况,可说着说着,她忽然眼前一亮,心里有了一个主意……
钟琂眼看她突然兴致勃勃地拿起手机打字,他好奇地问:“你想到怎麽分配了?”
“不是,我觉得不应该分配。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只要分配,那就永远做不到绝对的公平,总有人心里会有疙瘩。我在想,我们那栋楼老年人居多,腿脚都不太好,拿这笔钱加装一部电梯应该很合适。”
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也不愿意爬楼梯。平时还好,但凡买个米面油,或者外出回来提个行李箱,再遇着一个炎热天气,楼梯都能让人头疼不已。
沈时因住的老房子连个正经物业都没有,一切事情只要业主商议做主就行。她的这个想法一经提出,马上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响应。
沈时因说干就干,吃完饭坐在茶几前打开电脑,挨个研究电梯。
钟琂也坐在她旁边,摊开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沈时因做的笔记。
沈时因百忙之中抽空问他:“你该不会又要告诉我你有熟识的电梯厂家吧?”
“那倒没有,”
钟琂说:“不过我妈妈应该有认识的人,我可以帮你问问。”
“行,那你就打听打听,问个行情价。让我心里有个底就行。”
钟琂走进书房打越洋电话。不一会儿,他打开门说:“我问过了,目前最便宜的电梯十五万就能拿下。”
这跟沈时因预想的差不多,剩下的钱再分一分,把大部分补偿给一楼,小部分给二楼,因为一二楼的采光多少会受影响。作为方案的提出者,沈时因表示自己不需要补偿。
不知不觉间,沈时因已经成了整栋楼里各家住户心中的领头人。他们都觉得这件事交给沈时因全权负责最好,也最让人放心。
事情一旦确定下来,剩下的就只有实际操作了。沈时因高兴得在地毯上手舞足蹈:“太好了,房子做好了适老化改造,楼房也马上会有电梯,外婆可以安享晚年了!”
钟琂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沈时因,望着她出神,更因为她的一举一动而感同身受。原本空蕩蕩的居所因为沈时因的到来变得很不一样,增添了欢声笑语,让一栋冰冷的房子真正变成了家。
如果这就是他们结合之后本该会有的时光和岁月,那该有多好呀。
沈时因自顾自地欢呼完,注意到若有所思的钟琂,“你在想什麽?”
“我在想……你和我们那天在派出所见到的那对姐弟很不一样,你们代表了两个极端,你太美好了。”
“我还在想,如果我是你,我不一定能做得比你更好。”
“也不能这麽说。那老头脾气古怪,肯定没少虐待身边的人,外婆可没有苛待我。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那亲爸哪天出现在我面前,我肯定也巴不得他立刻去死。”
即便再小心谨慎,沈时因还是犯了忌讳。不过钟琂看上去一点也没生气,连出声制止她都没有。
沈时因鲜少提起她的爸爸,钟琂深知这是一个禁忌,一个只要提起来就会不愉快的话题。他没有接话,而是岔开话题说:“天都黑了,外婆怎麽还没回来?”
忽然提起那号人物,沈时因也有些意兴阑珊。刚才的好心情蕩然无存,她朝外张望道:“牌局应该快结束了,那我去活动中心接她。”
沈时因还没往外走出多远,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钟琂也追了出来,说要跟她一起。
别墅区的居民不算多,每栋房子之间又相距很远,走在小区里显得有些空蕩寂寥。路灯昏黄影绰,照在石板路上,钟琂和沈时因并肩而走,在地上留下拉长的、不时相交重叠的影子。
或许是夜晚太静,时间也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他们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耳边只剩脚步声和衣物摩擦的声音。
路过凉亭,沈时因听见潺潺的水流声。她不自觉地走上前,看见湖水里有许多游弋着的鱼群。
沈时因向前倾着上半身,钟琂赶紧在后面拉住她的衣摆,“你小心点,别掉进水里了。”
沈时因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往湖水里照,好多不明品种的大鱼都循着光亮聚了过来,各个张着嘴,仿佛嗷嗷待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