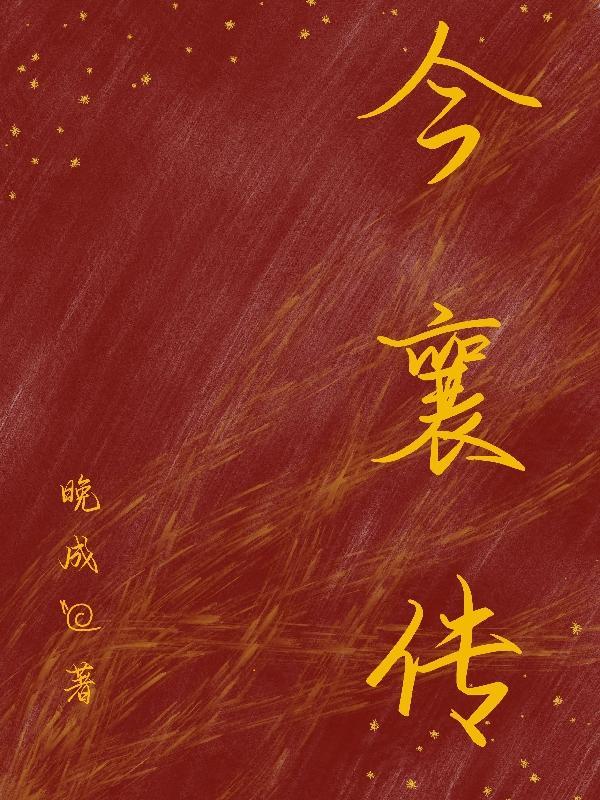搜读>夺权是什么意思 > 第六十一章 打算(第2页)
第六十一章 打算(第2页)
整个谢家,仿佛被蚀空了一般,除了谢娘子在时置办的一些大物件,其他的摆设装饰都是些廉价的东西,连他这个不识货的人也能一眼看出其品质低劣,恐怕当铺都不会收。
连国公府送的东西都不见了踪影,如果他猜的不错,这些东西应该好好地摆在王家。
“娘子,须知你嫁给了我谢焘,后半辈子是要在谢家过的,无论贫穷富裕,你都要在谢家过。这里,才是你的家啊!”
谢焘独坐在台阶上,月色如水,照在他身上,将影子拉的很长,映着镂空的窗影,显得孤独而惆怅。
直坐到第二日天亮,露水湿了衣衫,院子升起了一层薄雾一般的水汽。
一夜未睡的谢焘神色憔悴,他站起身,整了整衣衫,“去王家讨救命钱。”
细想起来,自从王氏掌管清风楼后,他已许久没见过王家人了。
王明山曾当众嘲笑他是窝囊废,说他惧内,只一个王氏便把他收拾的服服贴贴。而王母,亦瞧不上他这个只会读书的女婿。
他自然也不愿意和这家人打交道。
但眼下,是不得不去了!
谁知,他刚走出院子,就见王母着急
忙慌地跑来了。
谢焘作了个揖,说道:“小婿见过丈母。”
王母撇了他一眼,面现不耐,“行了,拜什么拜,都这个时候了,别整这些酸文了。”
她直截了当地问,“你家能拿出多少钱?”
谢焘被她问得愣了神,家都你女儿搬空了,还问他要钱?
“小婿没钱。”
他诚实地说道:“一文钱都没有。”
“就知道你没钱,也不指望你能拿出一文钱。”
王母后退两步,看了看门框上的匾额,“这宅子地段好,又是三进三出的院子,应该能值不少钱。”
谢焘听得心中一惊,问道:“丈母是打算卖了我这宅院吗?”
王母把郭氏卷钱跑路的事情简要说了,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她一句带过,反而质问谢焘,“如今王家拿不出钱,你又没钱,难道看你媳妇活活被打死吗?”
“这宅子至少能卖十万贯,再加上你哥哥弟弟的钱,还有你老母亲的钱,能救下你娘子一条命。那可是一条人命啊,女婿。”
这算盘打得,隔着十几里都能听到响声了。
不但他的宅子,连他兄弟、母亲的钱都算进去了!
“可这宅子是小婿前妻置下的,凝哥儿还在,卖不卖房子,我实是做不了主!”
谢焘实话实说,前妻临死前说了,这宅子是要留给儿子的,“再说,房子卖了,我们一家人要住到哪儿去?”
“至于叔伯兄弟,我更无权向他索要钱财,清风楼好时,他们没得一
分利,现在遭了难,他们也没有义务出钱。”
王母看着这个榆木脑袋的女婿,眼神中七分恼怒,三分不屑。
她直挺挺仰面倒地,开始哭天抢地,“老天爷啊,谁来救救我的女儿啊?你这个没情义的,宁可死了发妻,也要住大屋。你、你要遭报应,天打雷劈,死了要下十八层地狱。”
谢焘听着那与王氏一般无二的哭喊,捂住了耳朵。
突然,王母面前射过一支利箭,箭头没入土中,离王母的脸只有一寸,她甚至能清晰地看着银箭头上的花纹雕饰。
身后,谢凝束着襻膊,手持弓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