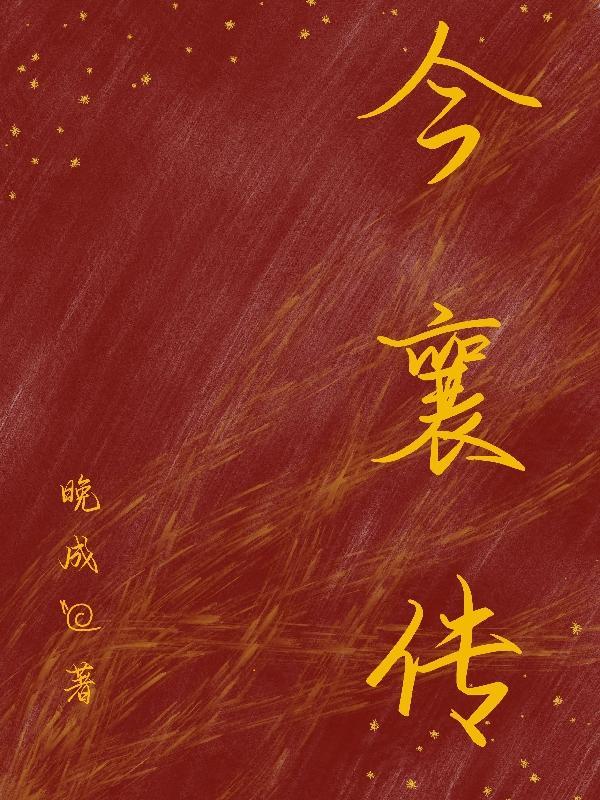搜读>夺权是什么意思 > 第六十一章 打算(第1页)
第六十一章 打算(第1页)
春娘听到声音,急忙抱着孩子赶来,当她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后,几欲晕厥。
那幢房屋是王明山留给她最值钱的东西,其他的金银细软虽说也能换些钱,但若要完好无损地赎回丈夫,却是不可能的。
况且,她也需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往后的日子,清风楼是指望不上了,她还想留些钱做些小生意。
现在看来,这些钱是留不住了。
等王母好不容易缓过气来,春娘狠了狠心,说道:“娘,明山曾在郊外购置了田地庄子,因地方偏远,不值多少钱,我本想等明山出来,变卖了换些钱度日。现在看来,只能先用它应急了。”
“我还有些首饰,也一并拿去当铺当了,能凑一点是一点。”
王母看着春娘,眼泪汪汪,“好孩子,你是个好孩子,明山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
眼下,能多出一文钱都是好的,就算不能免了板子,多给官差送些银钱,也能下手轻些。
春娘抱着孩子,起身去了。
王母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心里像被油煎一般难受,一面是恨极了郭氏,恨这个毒妇卷走了儿子女儿的救命钱,这么多年夫妻,竟不顾念一点儿夫妻情份;一面是感叹春娘的知情达理,在这紧要关头,不离不弃,是个难得的,待儿子回来后,一定要给春娘个名分。
可这些,都是后话。
当务之急,是把儿女弄出来,而且是全须全尾地弄出来,若是瘫了残了,
下半子成了废人,还不如死在牢狱,省得出来拖累别人。
趁当下没有行刑,得赶紧筹钱。
可是钱呢?
去哪里才能弄到钱?
她想到了谢焘,自女儿掌管了谢家,她眼里便再没有这个窝囊废,整日里除了掉书袋,说些酸话,屁大的本事没有。
但现在,这个窝囊废成了她眼中的救命稻草。
谢家的西耳房中,罕见地没有传来读书声。
其实不用王母来找,自王氏出事后,谢焘再也无心读书,四处托人打听,得知妻子被判了九十杖,他心急如焚。
虽然妻子平日骄纵跋扈了些,终究是个女人,这九十板子打下去,莫说是个女子,就算是行伍壮出身的壮年男子,也没有命在。
他平日里大多在书房,但毕竟年纪大,多少是有些阅历的,知道若想免去这顿板子,得有钱。
可惜,他的朋友不多,几个旧友也是如他一般的穷酸文人,勉强凑出十贯钱,还不够官差打牙祭的。
王氏日常银钱管得紧,除了吃饭、穿衣,他手里一文钱都拿不出。
谢焘为此愁得几宿睡不着,找人筹不到钱,那就去当!
前妻为谢家筹谋多年,多少是有些家底的,明日便去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当了,好歹得保住王氏的一条命。
想到这里,他再躺不住,夜里便去前厅后院找了个遍,看看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能拿去变卖,连两个女儿的闺房都没有放过。
可没承想,这一翻看,他
心里越来越凉。
王氏自来谢家后,不时拿钱贴补娘家,他是知道的。
王家过得潦倒,他也是知道的。
女子嘛,嫁人后舍不得娘家,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想给娘家送去,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娘子,你不该如此啊!”
谢焘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