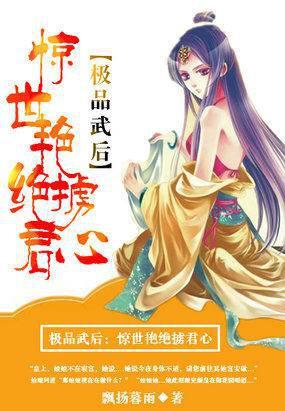搜读>大唐诡事历史背景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却听屈突宜忽然开口询问:“对了,不知李郎君在京中作何营生?”
李好问被问住了,顿了一下才道:“惭愧,不过靠着父母留下的一点点余财混日子罢了。”
屈突宜上上下下将李好问打量一回,突然笑着问:“敝司目下有个职位空缺,想要邀请郎君加入我司,李郎可愿意否?”
——这么好?
李好问心头一喜,但马上警觉。
他可没那么天真,认为自己喊对了对方的姓氏,对方就会真心当他是“好朋友”
,好心提携他,热情为他介绍职业岗位。
当然了,李好问最近确实是无业无收入的双无人员,仅靠母亲崔真留下的一点嫁妆维持家用。而且他也确实很需要钱,很多的钱,用来保住敦义坊的这座宅子。
对于屈突宜的提议,李好问也没有太高的预期:即使是大唐,应该也没哪个岗位的俸禄两个月就能买房的吧?
但他没有马上拒绝,而是谨慎地开口询问:“请问贵司是哪个职位空缺呢?”
屈突宜的视线下意识地就往郑宅大门上转去,转到一半,连忙打住,又转回来,唇角带笑,望着李好问。
这……李好问心头一跳,伸手在太阳穴上揉揉——他瞬间就明白了。
屈突宜今日来,根本不是试图招揽李好问加入诡务司,他是来物色郑兴朋的继任者的。
然而李好问怀疑自己可能遭遇到了求职诈骗。
他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没什么过硬的家世背景,从未被举荐入仕——他能继任长安一个正规职司的司丞?看屈突宜身上的绿袍,应当至少是从七品的官员,那么司丞的品阶显然要比这更高。
“屈突主簿,我想你一定是找错人了。”
李好问很冷静,对面抛来带饵的鱼钩他坚决不能乱咬,“我只是一个尚未及冠的少年,对贵司司务没有任何了解,万万不能胜任贵司的职务……”
他一面说这话,一面见到屈突宜嘴角向上略扬了扬,似乎对他的谨慎感到满意。
“李郎君,我大唐一向不以长幼论英雄。各职司选人只问是否合适,而不是计较其年纪履历。敝人自己昔日不过一名极寻常的道门中人,现在也一样成了主簿……”
李好问心道:那不一样。
“好比今日,敝人就听说了这样一个任命,一位刚刚及冠的年轻人被授以从七品宣义郎的官职。那位,可并不比李郎君你年长多少岁哦。”
李好问险些开口反问:“你跟踪我?”
他这才刚从庆贺此事的族老家中出来,屈突宜竟也知道此事了?
但他马上忍住了质问的冲动:族老一家恨不得将李好威得官的事炫得人尽皆知。再者,朝中官员的任免由吏部完成,屈突宜如果在那里有渠道,得到消息也不算太奇怪。
“话虽如此,但我有自知之明,贵司司丞之职,我决计无法胜任。”
李好问说着这话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这诡务司的司丞,如今应该是个人嫌狗不理的职位,朝官见了都躲的吧?
从建司至今,七任司丞,没有一位是善终的,每一位都莫名其妙地死在任上。最近一任的郑兴朋,又死得如此离奇诡异。
说实在的,他心里并不介意这种“离奇诡异”
,毕竟他从小就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人,选择了考古专业之后也是如此,枯燥的田野作业,艰苦的野外环境,都未有打消一分一毫他想要见证历史的好奇心,让他日复一日地扎根在考古现场挖啊挖啊挖。
但穿越之后,李好问就给自己拟定了规则:在完全回归科学的理性的世界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克制自己的好奇,不多说,不多问,不掺和。
出人意料的是,在李好问态度坚定地拒绝之后,屈突宜嘴角的弧度似乎更大了。
他没有因为李好问的拒绝而感到冒犯,而是温文尔雅地执手行礼:“郎君无须马上做决定,朝廷重新任命司丞还需一些时日,我等也需处理一系列杂务,并追索郑司丞的真正死因……”
李好问:看来你们也不愿相信上司是被屏风杀死的。
“……但郎君可以再多考虑考虑,也可尝试了解了解我们诡务司。另外……”
屈突宜眼神幽邃,凝望李好问片刻,忽然高深莫测地笑道:“万一郎君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不妨考虑一下我这个‘朋友’!”
李好问在心内频频摇头:他现在最急需的,就是想办法保住敦义坊的这座宅子。但这涉及家族和上一代的纠纷,他并不认为这是诡务司这么个官方机构能够办到的。
但表面上他与屈突宜虚与委蛇:“好的,屈突主簿,今日幸会。”
说毕他向屈突宜告辞,向西来到自家门前。
这时卓来手中捧着两个胡饼,一边叹气一边向李好问这边过来。刚才进敦义坊坊门时,李好问打发了他去采购一点吃食。
“郎君,张家大嫂今日还没从长安县回来!坊里再没谁能做她家那样的古楼子,这可怎么才好哟!”
李好问明白自家小厮为何会发那样的感慨——张大嫂着实是敦义坊内不可或缺的一位人才。
这位三十来岁的妇人是一位敦义坊土著居民。她男人叫张武,是个老兵,在战场上丢了两条腿,一家子都要靠张嫂的双手养活。是以她在自家烹饪饭菜供应街坊邻里,搞出了一个唐朝版的“社区小饭桌”
。
在郑家出事之前,李好问和卓来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张家搭伙,其中最念念不忘的美食就是张家嫂子做的古楼子。那古楼子就是将胡饼填入香料羊肉馅后送入烤炉内烤熟,烤出的成品表皮焦黄酥脆,内馅肉汁饱满而鲜美,是堪比后世肉夹馍、披萨饼和烤包子的美味,身为资深吃货的李好问十分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