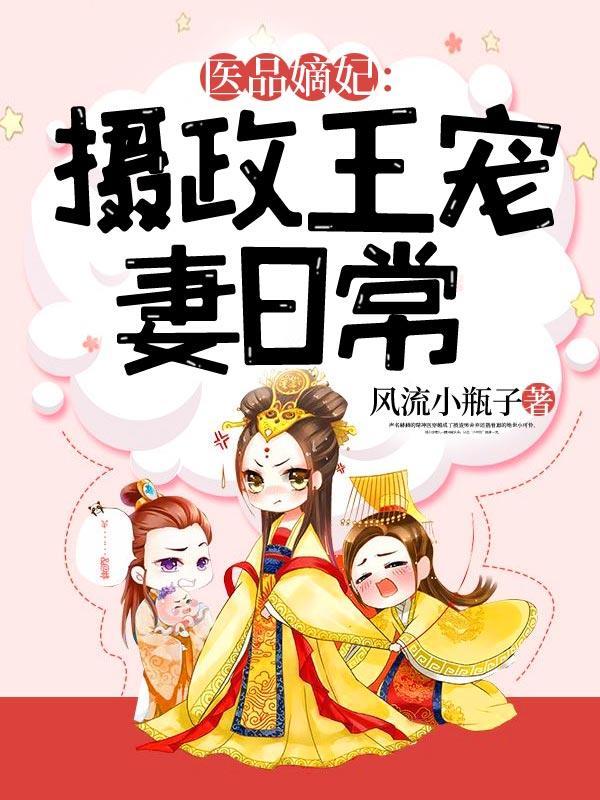搜读>九州仙侠传转生任务表 > 第六章 乱坟岗(第1页)
第六章 乱坟岗(第1页)
卢恒在庆丰镇外的一处山丘上显出身形,却是他不愿与人客套作别,厌烦那些凡尘俗礼,索性施展了小挪移之术,一步便出了镇外,这也是卢恒的极限了,转瞬三五里,传说中有大挪移之术,一步便是千万里之遥,但那只是仙人的手段,;卢恒却不敢想象。
摇了摇头,卢恒也不去想那些遥远的事,这里只是他下山的第一步,将来的路还长得很,自己也要游遍九州,增进自己的道行,也不枉师傅的一番期望,想道这,卢恒盘膝而坐,将得自野猪精身上的内丹取出,自己道行太浅呀,这次若非剑利,若非自己先行偷袭,让那野猪精受伤在先,使得野猪精无法使出全部法力,以自己的道行,这次怕是便要栽在这里了,当务之急,自己便是要提高功力,本来提升法力非是一朝一夕之功,但这野猪精的内丹,却能让自己省却两三年的苦修,怪不得师傅说过,便有许多名门子弟,为了提升法力,不顾天心,刻意制造杀戮,得取妖怪的内丹,以至与天下的妖怪无论好坏都与修道人势同水火,自己却要牢记师傅教诲,当要明辨是非,不能不教而诛,当年师傅便能为一初开灵识得小狐狸而与昆仑前辈扛上,师傅便是自己的榜样。
记得师傅曾说过,修行路上本是千难万难,更是要顺其本心,多积德行善,本一颗善良之心,但修道本是逆天而
为,却要心性坚韧,有时除恶既是扬善,当是除恶勿尽,容不得半点心动。
野猪精的内丹在卢恒头上悬浮着,就像无形中有一只手托着,卢恒一点点吸纳这内丹的灵力,却也不忘吸纳天地间的日月精华,就在这荒郊野外缓缓入定,修炼起无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卢恒突然被一丝灵动所惊扰,从禅定中醒来,此时也是月上柳梢头只是,只是不知又过了几许时日。
那一丝灵力的波动很隐晦,若不是卢恒是在入定中,怕也注意不到这丝隐晦的灵力波动,卢恒站起身,朝那波动传来的方向望去,却是十几里外的一处乱坟岗,卢恒皱了皱眉,一个小挪移,便现身在乱坟岗上,卢恒的骤然出现,显然惊扰了那个波动,还未待卢恒神识探查出波动的所在,那丝波动却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卢恒环目望去,这是一片好大的乱坟岗,不知几代,怕不有几里方圆,鬼火点点,卢恒的出现,惊吓了几只正在抛尸的野狗,吓得它们夹着尾巴匆匆逃走,树上呼啦啦的飞起不知多少夜猫子,若是普通人在这样的地方会有何感受。
那丝波动既已消失,卢恒却也不着急,便如散步一般,在这乱坟岗上信步闲庭,慢慢走动,却还恶作剧般,摇头晃脑的吟起诗词:今时明月西墙柳,与君相邀到小楼,举杯同饮一杯酒,往事不堪去悠悠。唉,只是无人欣赏,可
叹呀。
逛了大半夜,那丝波动终究未再出现,这让卢恒也很是无趣,待到天明,路上便有了耕田的农夫,远远望来,看卢恒一个人在乱坟岗上转悠,只道这小子怕是昨夜走错了路,在这乱坟岗上碰到了鬼打墙,怕是在这转了一夜了,此时天已大亮,还未曾从磨中醒来,若无人相告,怕是不知还要转到什么时候,当下,便有一个好心的大叔走进乱坟岗,冲着卢恒大喊:“嗨,天亮了。”
卢恒回头看了那大叔一眼,抬头又看看天,心里倒是有些奇怪,难道我看不出已经是早上了吗,干嘛还要告诉我,太阳都出来了,还说天亮了,当真奇怪。
那大叔走到卢恒身边,拍了拍卢恒的肩膀,道:“你是那村的后生,你家长辈没同你讲嘛,怎么还晚上路过这乱坟岗,不知这乱坟岗夜里是走不的得嘛,你这孩子,胆可真大,快回家吧。”
卢恒听罢,却大略听出个什么意思,感情这位大叔是当自己是附近村子的人,以为自己昨夜路过这乱坟岗,结果被鬼缠了,碰上了鬼打墙,虽不知鬼打墙是怎么回事,但稍微一琢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想必就是半夜行路,碰上那个顽皮的鬼,开了个玩笑,让行路的人在此转了一个晚上,想来也不是什么恶鬼,开个玩笑,却不知给行路的人造成了困扰,却也该骂。
“大叔,谢谢你了,要不我还要在这转呢。
”
卢恒微微笑着,虽不拿这当回事,但却谢得很真诚,毕竟这位大叔却是真心诚意的帮他。
大叔摇了摇头,看着卢恒不以为然的样子:’唉,你们这些小辈,怎的胆子就这么大,转了一夜还不知道怕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
卢恒点了点头笑道:“是呀,大叔,其实我是昨夜听的有动静才过来的,到不知这乱坟岗上有些什么故事,能说给我听听吗。”
“行了,打听那些干嘛,赶快回家吧。”
大叔有些不耐烦的挥了挥手,瞪了卢恒一眼:“你这后生怎的不懂事,这乱坟岗上有冤魂,都闹了一年多了,去年还吓死了一个郎中,以后别来乱坟岗了,否则指不定那天被鬼缠上,枉送了性命。”
“大叔,您说这乱坟岗上有冤魂,这是怎么回事,能讲来听听嘛。”
卢恒好奇的看着大叔。
大叔哼了一声:“我还要下地干活,哪有时间和你磨嘴皮子,反正告诉你了,以后最好别来这乱坟岗,你是爱听就听,不爱听拉倒,那天丢了小命,别怨大叔没提醒你,行了,不和你这小娃子瞎配了,我去地里干活了,你快回家吧。”
大叔说完,扭头就走,也不再管卢恒听不听他的,毕竟他只是个普通的庄稼汉,管不得那许多闲事,他却还要指着地里打出粮食,好养活一家人。
卢恒却不着急,大叔前面走,他就在后面慢悠悠的跟着,一直跟到
大叔地头上,看着大叔在地里干活,卢恒便找了个树荫坐下,远远喊道:“大叔,怎么称呼呀?”
那大叔却不理睬他,自顾自的干活,心道:这哪来的后生,怎的这般讨厌,转了一夜,也不怕鬼来着,还不快点回家,却跑来烦我。
卢恒见大叔不理睬他,也不着恼,看着有些干裂的地陇,喊道:“大叔,这地太干了,该浇水了吧,要不这庄稼怕要少打不少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