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读>穿成暴君的早死白月光_钱八方 > 第93頁(第1页)
第93頁(第1页)
怎麼聽起來跟快哭了似的?
祁景言慢慢皺起了眉,銳利的視線掃視一圈,語氣下意識變得柔和:「怎麼了?我在呢。」
「有點餓,還很累,」宋辰安用手指了指頭上的冠子,「這東西現在能取下來了嗎?壓得我脖子疼。」
祁景言正要幫他取下,喜娘又在勸:「王爺,這真的不合規矩,這冠子應該在就寢的時候再……」
真是聒噪。
祁景言正想把喜娘打暈再丟出去,省得讓人心煩,卻聽到宋辰安喊疼:「哎呀,纏著頭髮了。」
他小心地取下頭冠,在手上掂了掂重量,確實不輕。
「頭冠戴著不舒服怎麼不早點取下來,何苦這樣為難自己?」
宋辰安嘿嘿一笑:「今天可是咱們成親的日子,我想每個環節都儘可能完美一點,這樣等我們老得走不動了一起回憶過去,最起碼不留遺憾嘛。」
他三言兩語就打消了祁景言方才的念頭。
不僅如此,還頗為贊同:「安安說的是。」
喜娘絲毫不知道自己躲過一劫,盡心地說了一大串吉祥話。
什麼「郎娘,像對鴛鴦」,什麼「天上下雨地下流,夫妻恩愛到白頭」。
到白頭啊,宋辰安有些恍惚。
也不知道他和祁景言有沒有機會到白頭呢?
這之後,就是二人喝交杯酒的環節。
祁景言對這個喜娘忍了又忍,最終實在嫌她話多,封了賞錢把人請走了。
宋辰安坐在桌子旁捂著肚子笑,笑完了,再為他們各自倒一杯酒。
他不怎麼飲酒,但今天是婚夜,交杯酒還是要喝的。
祁景言端過酒杯,兩人的胳膊繞過來,然後同時飲下。
酒很沖鼻子,度數應當不低,這是宋辰安的第一反應。
辛辣的酒液下肚,頭腦很快就變得昏昏沉沉。
「安安,你是不是該改稱呼了?」
放下酒杯,祁景言目光灼灼地望過來,眼裡滿是期待。
可是身為一個男人,叫另外一個男人「夫君」或者「相公」,總感覺怪怪的。
宋辰安有些難為情,期期艾艾地問:「王爺覺得呢?」
「安安叫聲相公來聽聽。」
說話間,祁景言輕輕一拉,人便被困在懷中。
「相公……」
宋辰安有點兒頭暈,眼神也變得飄忽不定,慢半拍地眨了眨眼:「相公,你怎麼變成兩個人了?」
祁景言聽了只有無奈,將酒壺放遠一些:「這酒太烈,安安都喝醉了。」
喝醉的宋辰安很是鬧騰,話變多起來,表情也更加豐富。
這是種很奇的體驗,祁景言任由他鬧騰,唇角含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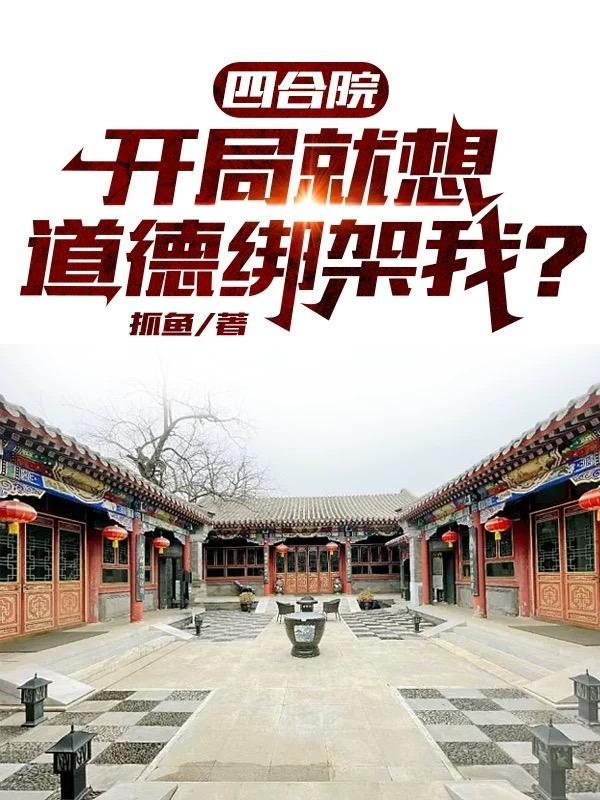
![[演艺圈]死灰不复燃](/img/3200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