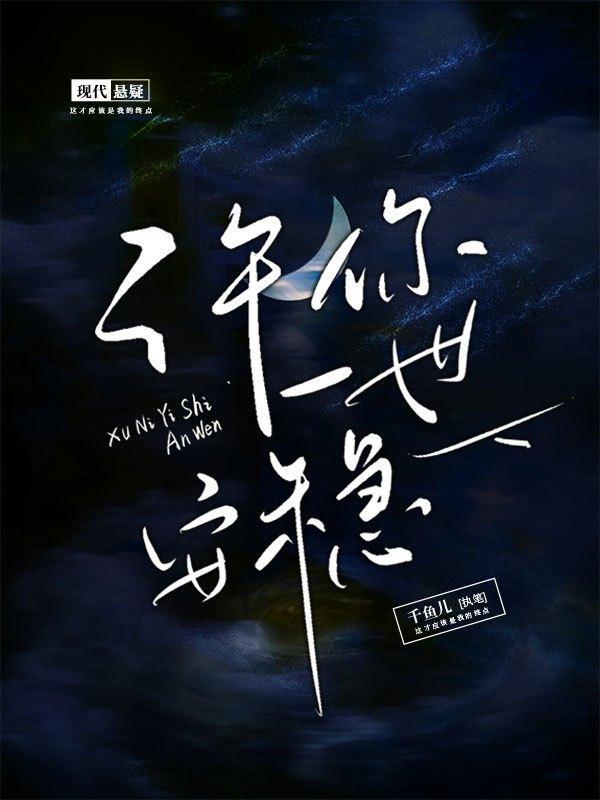搜读>维多利亚hyde > 第十二又二分之一章 怎么回事(第1页)
第十二又二分之一章 怎么回事(第1页)
她有一头诡秘莫测,美丽动人的靛蓝色直,她把它扎成了漂亮的马尾;深蓝色的眼睛大而尖锐,左眼睫毛下有颗泪痣;鼻梁和我一般高;嘴唇比我的稍厚些,并且更加红润;下巴也有一个较小的弧度,显得很英俊。
她的脖子长而白;肩膀和柳腰一样娇小可爱;但**和臀却很大;腿也丰满而长,脚更是小巧玲珑,优美可爱。
唔,按身材来说,她绝对是个大美人,但是这并不是她吸引我的全部理由——我之所以爱她,主要是因为她独一无二,特立独行的性子。
我初寄到她家时,我同她讲话,她总会摆出一副厌恶至极的面孔,我以为她嫌恶我,便准备自行离开——我收拾好行囊,在房间内恸哭,她不厌其烦的推开了门,准备讽刺我一顿——但在见到行李后就又愣了神,然后又劈头盖脸的教育起我来。
那时,我便知道她实际上不想让我走,擦擦泪,边笑边哭的开始重新铺床——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对她有了情愫,并在日后的相处中长成了一整片森林。
她从不在乎在我面前褪衣,擦身,亦或是其他的暴露行为,甚至有时我也会参与其中。那时我大概是十六七岁,正是青春萌动的时候,我壮着胆子向她袒露心声。
我当时说:“我爱您。”
,她说:“您若是想玷污这副身体就随您的便吧。”
,我又重复了一遍。
她觉得烦躁了,便直接将我拉在她的怀中,问我该从哪开始。我呢,继续重复着那三个词,她脸上才浮现出疑惑不解的神色。
她问我:“您既然爱我,为何又畏畏尾,不敢动作?”
;我反问说:“我既然爱您,怎能只贪恋美色,买椟还珠?”
她不知道为何,难得一见的有些生气了,整张脸上都冒出些愠色。她开始粗暴的撕扯我的衣服,我没有挣扎或是反抗,她就强迫我同她交媾。
(话到此处,叶列娜面红耳赤的扫了一眼维多莉娅。)
那之后,我问她是否爱我,她说她恨世上的每一个人。我当时真是坚毅要命,非得从她嘴里听到那个词,撒泼打滚的纠缠她。
她终于不耐烦了,就敷衍着说了。
我却仍不肯放过她,一旦有时间就必会同她争论不休——不过现在好多啦!
我天天都可以见到她,我还能为她做很多事,她的衣食住行都由我操办,我感觉自己能真正帮到她了——美中不足的是,她依旧不肯回答问题,只在少数时候同意我的需求,不过这也很不错啦。
唔,我还是挺容易满足的人,尽管我要死要活的爱她,但我既没办法身心俱得,便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得到前者了。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您觉得您该如何做:我觉得就是要用同等的爱去灌注她,您可以为她做很多事——就像我一样,我只是为她办事,能够见到她就心满意足了。
(“她若是信教,或是接受不了该怎么办呢?”
维多莉娅迟疑的问道。)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她既然不肯受您的心意,那维持之前的关系就算不错了。
但我并不是鼓励您不去表达——我的意思是,朋友的关系总会有一个顶点,那便是每种关系都会有的桎梏。
一旦过那个顶点,它势必会变成一个新的关系。有时,它们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转变的。
-----------------
“□?,?。?(还有这事?)”
帕丝缇轻轻环住维多莉娅的脖子,捂住她的耳朵。讽刺的朝着她笑着。
“□?,?。?(跟您什么关系也没有。)”
溟涨皱皱眉头,扒在运河外侧的栏杆上,她凑到叶列娜的身前,盖住了她那伤感与喜悦并行的声音。
“您捂她的耳做什么?”
“那您遮她的口又是为何呢?”
“我不想听见她讲话。”
溟涨摊了摊右手,嘲讽的笑了笑,露出了她的那排尖牙利齿。
“您来这什么事?”
“我把《mountain》杀了。”
“您杀它做什么?”
帕丝缇瞥了溟涨一眼,“专门为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