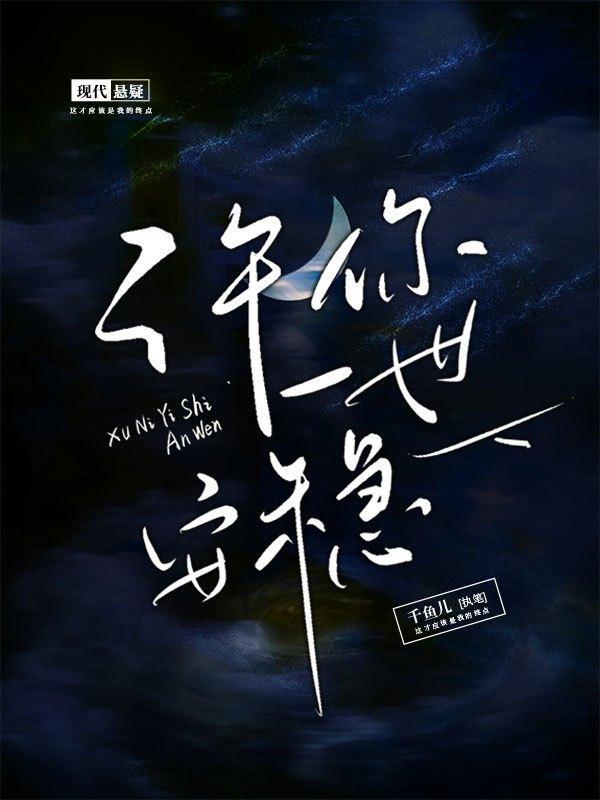搜读>糟蹋白莲花什么的最喜欢了!好看吗 > 47第四十七章(第1页)
47第四十七章(第1页)
傍晚之前,他们掘成了战壕。江对面的枪炮上时断时续,那必然是一场苦战。叶荣秋坐在战壕里,黑狗就坐在他身边,两个人都在愣,谁也没有搭理谁,但是谁也没有主动离开对方。
叶荣秋现在很茫然,他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已经到了上战场,他不停地掐着自己的手指,希望能从如此虚幻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可惜手指已经疼的麻木,而他还是呆在这个鬼地方。不过他没有后悔,他不愿意去想刚才的事情,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逃跑的机会,回忆已经做出的抉择只会让他更加难受。他开始在脑子里拽一些文绉绉的句子,可惜现在没有纸笔让他写下来他在构思他的遗书。
老兵们已经学会了一套自行舒缓压力的方式,他们在战壕里说说笑笑,完全不像是在战场上,倒像是饭的闲聊。
刚才掘壕时和叶荣秋说话的东北人叫田强,他身边还有两个人,一个叫马霖的广东人和一个叫皮胡的河南人,他们三个就在叶荣秋边上,自从钻进战壕后就一刻没有停止地吹牛。叶荣秋听着他们天南海北的口音交织在一起,心想这支杂牌军实在杂的无药可救。
马霖说“你们猜猜,江对面还能支持多久”
田强哼哼“打得久一点呗,替我们多消耗点小日本的炮弹。”
皮胡神神颠颠地掐指算了算,高兴地说“今晚是打不过来啦。”
马霖斜了他一眼“你怎么鸡道啊”
皮胡学着他的口音“我就是鸡道啊。”
他亮出刚才掐算的手指“我算了天相。”
“嘿,。”
田强说“瘪犊子玩意儿,你啥时候整的会算命了”
皮胡说“我爹就是给人算命的,我跟他学的。”
马霖说“你上次还说你爹是医生啦。”
田强吃吃地笑“你信他他驻马店人,驻马店人最会吹牛。”
“嗛。”
皮胡不屑地说“给人看病就不能兼职算命你们别不信,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出生的时候我爹就给我算了一卦,说我能活到七十七岁。我看你们顺眼所以给你们透个风,等会儿跟紧了我,子弹炮弹都不兴往我这飞,我罩着你们。”
马霖撇嘴“你爹是巫医啊。”
田强说“驻马店人。听他胡扯。”
皮胡在同伴那里得不到吹捧,不满地哼了一声,转身来跟叶荣秋搭讪。他笑嘻嘻地说“小哥,我给你算一个”
叶荣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把头低下去了。他心情很低落,没兴趣跟人吹牛。
皮胡碰了钉子,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自说自话地热络“来来,我给你算算,手拿来给我看看。”
他拿起叶荣秋的手装模作样地看了起来,叶荣秋没有反抗。
“哎呀呀。”
皮胡惊呼道“你这个命势嘶哎呀”
他看完了却不说话,故弄玄虚地卖弄起来。
叶荣秋抬起头麻木地看着他,显得兴趣缺缺,只是看着他,没有问。
皮胡的两位朋友在一旁帮忙喝他的倒彩。马霖说“信他就有鬼啦。”
田强说“驻马店的人说的话那能信”
皮胡没有得到捧场,面上讪讪,哼哼两声,自顾自说了下去“你瞧你这里,你命里有个大劫啊。我算算哎呀,这个劫就是这两天呐。你要是能把这个劫过去喽,你后头这命就顺了。你打这场仗可要当心了。”
田强嗤笑“话都让你整完了。”
叶荣秋这场仗要是死了,那是他算出来的大劫;要是没死,也是他算准了,以后是好是坏,谁又知道呢。
马霖凑过来“比我睇睇给我看看。”
他接过叶荣秋的手掌“大劫在边度哪里啊”
皮胡有木有样地指了指叶荣秋心里上的一条线。马霖把叶荣秋的手凑到眼下仔细看了会儿,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抠了抠,就把皮胡所说的那道劫给抠了。“什么啊是道泥印子好不好还大劫劫你个头啦”
周围的几个家伙都吃吃笑了起来。
皮胡倒是一点不心虚,猛地拍了下手“哎呀哎呀神仙哪”
他对叶荣秋说“小哥,他活神仙把你这道劫给破啦你以后都能顺顺利利的”
几个人哄堂大笑。
叶荣秋没有笑。但是拜他们所赐,他停止了对自己遗书的构思,心情没有那么低落了。
黑狗一直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时也不由会心一笑。他侧过头看了眼叶荣秋的侧脸。叶荣秋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忧郁,不再是那个目中无人的大少爷,也不再是那个依赖的他要命的小白猫。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突然觉得叶荣秋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成熟稳健了不少。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
叶荣秋脸上有几道泥印子,黑狗伸出手想帮他抹去,但是他的手还没碰到叶荣秋就被叶荣秋狠狠拍开了。他无所谓地耸耸肩,望着天空呆。
孟元凑过来,笑嘻嘻地说“黑狗哥,你再给我讲个故事吧,。”
黑狗说“先攒着,打完了仗,回去我给你讲两个。”
直到天黑,日本人也没有打过江来。顾修戈不停用望远镜观望着江对面的形势。他跳到战壕里,沿路踢着士兵们的屁股“都给我打起精神,准备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