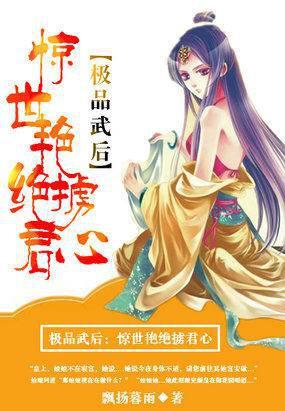搜读>深夜小狗神秘事件想反映什么 > 第35页(第1页)
第35页(第1页)
四、草原上有星星点点的野花。
五、远处有一座村庄。
六、草原边上有座围篱,围篱上有一扇门。
然后他们就不再注意其它细节了,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想些别的,例如"啊,这里真漂亮",或者"我好像忘了关煤气炉",或者"不知茱丽生了没?"{12}
但假如是我站在郊外,我会注意到一切钜细靡遗的细节,例如,我记得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三那天站在郊外的田野上,那天父亲、母亲和我一起开车到多佛搭乘渡轮去法国,车行路线是父亲所谓的"风景路线",意思是走乡间小路,然后在一个公共花园停下来吃午餐。途中我要求停车尿尿,我走到田野中,那里有几头乳牛,事后我停下来欣赏风景,注意到以下几件事:
一、草原中有十九头乳牛,其中十五头是黑白相间,四头是白褐相间。
二、远处有一座村庄,清晰可见三十一栋房屋和一座教堂,教堂的塔楼是方形,不是尖的。
三、原野中有田垄,这表示中古时期这里是所谓的犁田,住在村子里的居民家家户户都有一块农田。
四、树篱间有一个旧的阿士达市塑料袋,还有一个压扁的可口可乐罐,上面爬着一只蜗牛,另外还有一长条橘色的绳子。
五、田园的西北角地势最高,西南角地势最低(我有一个罗盘,因为我们是出去度假的,而且我希望到了法国以后知道史云登在哪个方向),田园就沿着这两个方位之间的连线略略向下折叠,因此,假如这片田园地势平坦,那么西北角和东南角就会显得略低。
六、我现这里有三种不同种类的青草,和两种不同颜色的野花。
七、大多数乳牛都面向上坡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另外三十一个小细节,但雪伦说我不需要把它们全部写出来。换句话说,如果我到了一个全的环境,我会感到非常疲倦,因为我观察入微,假如有人事后叫我说说那些乳牛长什么样,我会问他指的是哪一头,我还可以在家中把那头乳牛画出来,告诉他某一头乳牛身上的花纹是这样的。
我在第十三章的地方撒了个谎,我说"我不懂笑话",其实我懂三个笑话,其中一个是有关乳牛的笑话。雪伦说我不用回头去改十三章那句话,因为它不算撒谎,我只要"澄清"一下就好了,没关系。
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有三个人同在一列火车上,一个是经济学家,一个是逻辑学家,另外一个是数学家。火车刚刚越过苏格兰边境(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苏格兰),三人从车窗望出去,看见田园中有一头棕色的乳牛(乳牛站立的方向与火车平行)。
经济学家说:"看,苏格兰的乳牛是棕色的。"
逻辑学家说:"不,苏格兰有乳牛,其中至少有一头是棕色的。"
数学家说:"不,苏格兰至少有一头乳牛有一边是棕色的。"
这个笑话很有意思,因为经济学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逻辑学家的思虑比较清晰,但数学家说得最好。
我每到一个环境,因为看得很仔细,就会像一台计算机同时做太多事一样,导致中央处理器塞爆了,再没有其它空间想别的事。加上到了一个环境,又有许多人在场,情势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人不像乳牛或花草,他们会找你说话,做出令你始料未及的事,所以你必须随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注意任何其它可能生的事件。有时我在一个陌生环境,又有许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会出现计算机当机的现象,迫使我不得不闭上眼睛、掩住耳朵呻吟,就好像同时按住"ctr1+a1t+de1"三个键一样,把正在执行中的程序关掉,使计算机关机之后再重激活,这样才能记得当时要做的事,以及我要去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我擅长下棋、数学与逻辑的原因,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盲目的,他们看不清事实真相,他们的脑子里虽然有不少多余的空间,装的却是毫不相干而且毫无意义的东西,好比"我好像忘了关煤气炉"这种事。
181
{12}这是千真万确的,我问过雪伦,人们看到东西时都作何想法,她就这样回答我。
我的玩具火车组中有一间小房子,里面有两个房间,由一条通道隔开,其中一间是售车票的售票处,另一间是等候火车的候车室,但史云登的火车站不是这样,它由一条地下通道和几段阶梯、一家商店、一家咖啡屋,和一间候车室组成,如这般:
第33节:我好想回家
但这也不是非常精确的车站示意图,因为我太慌张了,没法子细细观察,这只是就我记忆所及约略画出的"概略图"。
那种感觉就像迎着强风站在危崖一样,令人头晕目眩、摇摇欲坠。大批人潮进出地下通道,回音嗡嗡,而且只有一个入口直接通往地下,通道内还有厕所的尿骚味和烟味,令人作呕。我紧贴着墙壁,手上紧紧抓住一块告示牌的边缘,以免跌倒而趴在地上。告示牌上写着"寻找停车场的旅客,请利用对面售票口右侧的电话寻求协助。"我好想回家,又不敢回家。我想拟订下一步计划,但眼前要看、要听的东西太多了。
于是我用双手掩住耳朵遮挡噪音,费力思索。我想到我必须留在车站搭火车,我还必须找个地方坐下,但车站门口附近无处可坐,我必须走下地下通道。所以我对自己说---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大声说出口---"我要下地道,那里或许会有地方让我坐下来闭上眼睛想一想。"我集中精神看着地道尽头的一块牌子走下去,那块牌子写着"警告:闭路电视作业中",那种感觉仿佛刚离开危崖又走在高空绳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