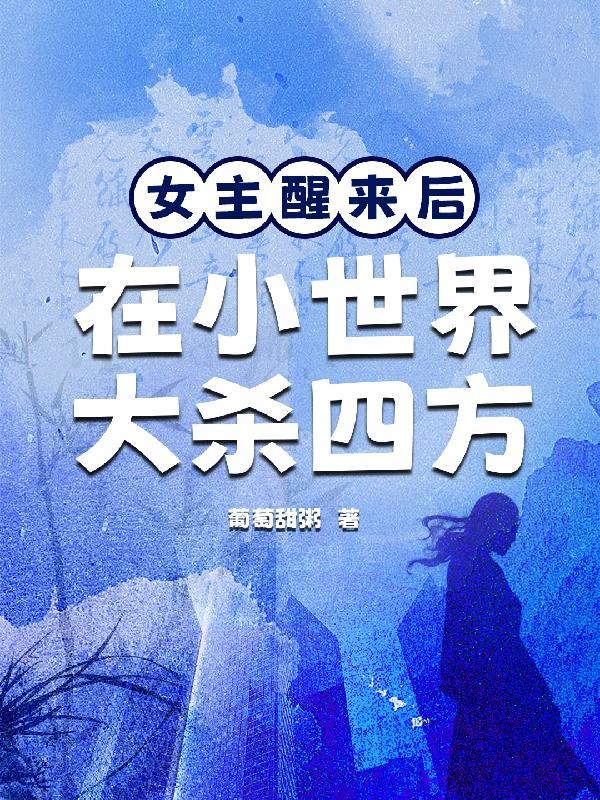搜读>重姒(双重生) > 第86章 仁善(第2页)
第86章 仁善(第2页)
谢重姒有些失望地将纸鸢扔给仆人,在他旁边坐下,凑过来个脑袋,“这是什么呀”
宣珏提笔的手顿了顿,温声道“前朝王密所作地志和民俗概览,残旧古卷了,誊抄一遍,有些对不上的我注释修改。”
说的对不上,自然是和他这一年来的经历对不上。
谢重姒也便问了“对不上和什么对不上呀”
宣珏“南来北往时,各地民风异俗,和几百年前多少不一样了。”
谢重姒来了兴趣,捧着脸,撑在石桌上,两眼亮地看着他道“哇,和我说说呗。我正儿八经离京,就去了趟江南三两地,整个大齐忒多地儿未到。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好看的呀”
“珏也未曾到过太多地方。”
宣珏抿了抿唇。
各地有各地的荒乱,各处有各处的压迫,皇权为天,氏族横贯,天地不通,九州大地之下生民陷水火。
谢重姒却不依不饶,撒娇地眨眨眼“说说嘛,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真的很想听。当时我就想和你一块儿去的,可惜没去成。民生百态,各地风俗,或者是你印象深刻的,都可以说呀。”
她双眸闪亮,春日柔光尽皆撒入,像是一簇春里新生的希望。
宣珏静默看着她,缓了缓,才轻轻颔“好。”
那日,宣珏也只照着王密那本风俗概览,断断续续讲了些各地风俗。没有涉及任何他参与的事情,像个局外人。
谢重姒却听得津津有味而且找到了隔三差五能来看他的借口。
一个月后,到了仲春之时,海棠花也开得正好,谢重姒一边抱来一堆烂漫鲜花,在回廊坐着插花,一边听宣珏讲着北漠的游民,她回头问道“诶那你喝羊奶了吗”
宣珏点头“喝了一小盏。之后没再敢喝了,很膻。不过羊奶入茶,味道很好,殿下你应会喜欢。塞北的游民会夜间燃篝火,那边没有氏族,民众也散乱自由,风俗热烈,有赛马狂歌的季节。我”
他察觉到谢重姒眼中熠熠的兴趣,说起自己来“我尝试和他们猎射几回,根本比不过最好的草原儿郎。”
谢重姒也听叶竹说过,揶揄眨眼“那些大胆奔放的草原姑娘们,有没有投掷鲜花给你呀”
“有。”
宣珏虽然不想说,但依旧实话实说,说完又急急忙忙找补,“不过我未接。殿下,我只接过您的那株牡丹。”
这话说得意味不明,说完宣珏才反应过来过于隐喻,但谢重姒愣是没大听出来,或者听出来,也大大咧咧觉得没什么,反倒有些可惜花来“唔,可惜啊,草原鲜花不易得,你收起来卖了当盘缠也好呀。出京本就没带多少银钱吧”
说着,将插花妥当的瓷瓶一摆,得意洋洋地道“怎么样叶竹总说我插花手艺太烂,但我觉得吧,应该还行”
宣珏“”
红绿交杂,吵到他眼睛了。
也不知是这花乱眼,还是谢重姒那慢半拍的反应让人头疼,宣珏无奈地扶额,说道“很不错。殿下,给您念句北漠的歌谣吧。春日行,很合今儿时辰美景。”
他直接念出听过几遍的歌谣,声调徐徐,也若春风和煦“献岁,吾将行。春山茂,春日明。园中鸟,多嘉声。梅始,柳始青。泛舟舻,齐棹惊。奏采菱,歌鹿鸣。风微起,波微生。弦亦,酒亦倾。入莲池,折桂枝。芳袖动,芬叶披。”
他隐没了最后一句未出口,只将前面的歌谣献上,谢重姒听得津津有味,收敛皇女全部的骄纵,问道“还有别的歌谣没有呀词韵好美,不像北方人写的,倒像是南方水乡才能养出的。”
“作歌者由南以北定居,早年确实不在漠北。”
宣珏轻轻笑道,“没了,以后想起,再念给殿下听罢。”
就这样,宣珏除却讲起风俗经历,也会偶尔念几句歌谣词赋。
谢重姒也是这个时候,现这人记性极好,几近过目不忘的,若若能入仕,决计远他父兄能达到的成就,可事已至此,她不敢流露惋惜,怕蜇伤宣珏,只能继续缠着他说些无关痛痒的游历。
她从半月一来,到五日一扣门,再到三天冒个头,再到最后,每天都来吵嚷玩闹,用她最不喜欢写的簪花小楷帮宣珏誊抄摘录。
这本书卷写到最后四分之一的时候,宣珏不再仅仅只和她提及纯粹一年来经历了。
那些经历见识里,会掺杂几分民生治理,和对百民的忧虑同情
这才是谢重姒从未听过、一无所知的空白地带。
她听得茫然彷徨,甚至有几分德不配位的惶恐
会有百越乱民为了一个脏馒头,争打地头破血流,会有失夫的贫妇抱子乞讨无法,最后被逼卖身,也会有瘫痪数十载的老者,家里实在无法照料,一根白绫送他上路。
那她呢只是生得命好,就享受唾手可得的富贵锦绣吗
皇权冷铁,尸骸堆砌,天金阙下尘埃不可见。
谢重姒本以为一切本该如此,当权者,纵横捭阖,谁都可以当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