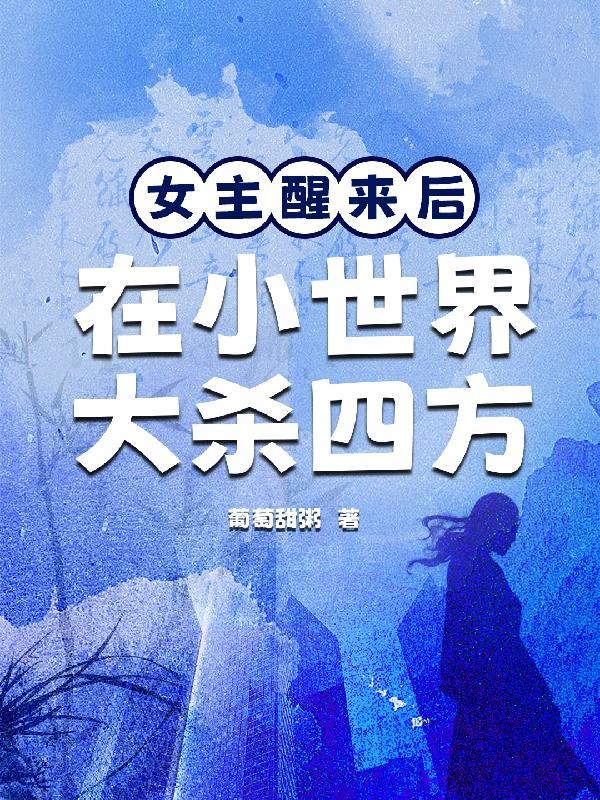搜读>三国吕布之女叫什么 > 第12章 我爹是吕布12(第1页)
第12章 我爹是吕布12(第1页)
吕布很是惭愧,道:“昨日我并没有看清,差一点就……”
他自责极了,道:“都怪布无用。”
严氏待还要再说,吕娴便进去了,道:“父亲,母亲。”
“娴儿……”
严氏忙拉了她进来,道:“昨日才刚伤着,怎么今日又折腾起来?!”
“我并无伤着,”
吕娴道。
“我儿,昨日为父对不起你,”
吕布面有惭色道:“差一点误伤我儿。”
“父亲该去与貂婵好好解释一二,貂婵一心一意只在父亲身上,父亲却疑她与旁人有私,实在过份。”
吕娴道。
吕布更是惭愧不已,忙道:“我且去看看她,与她道歉,她便是不肯原谅我,我便厚脸皮,好语相求当是……”
说罢摆脚就走。
“将军……”
严氏噎了一下,看着吕娴,伤心至极,道:“连你也向着貂婵了,她莫不是什么精怪不成,勾的连我亲女也向着她了……”
说罢又哭。
吕娴扶着她坐了下来,道:“母亲听我好语。”
严氏好哭,却是个没主张的人,与吕布性格相似。虽抱怨,却绝不是心狠之人。
吕娴虽不耐烦,但想一想,这些日子的变化,严氏心中也是惶恐的,她也没有好好的安慰过一回。如今,便只得耐下性子,好好的与她说一说家里的事了。
严氏道:“你有何话好说?!”
说天下大事,严氏是不懂的,吕娴只能从家事上说,道:“昨日之事本是家事,可是,我们温侯府却在整个徐州城闹的沸沸扬扬,名声实在难听,母亲可知?!”
严氏怔了一下,呆呆的看着吕娴。
“本是无事,也要被他们传出貂婵在家与人私通的话来,貂婵无不无辜家人皆知,累了她名声,女儿实在是祸害,本是玩闹,她因与女儿年纪相仿,我又无姐妹兄弟,便将她当成同辈之人相交了,结果闹成这样,人尽皆知了。可知外面人怎么传貂婵,传父亲,传我们家的不是?”
吕娴道。
严氏根本没想过这一层,道:“是我叫人通知诸人的时候,定是泄了什么……”
又道:“娴儿绝不是祸害,别由他们瞎说。”
严氏十分忐忑,一想外面的言语中伤,又惶恐起来。
“外面人怎么耻笑父亲,笑我们家不说,只说此事,其实可以完全避免的。”
吕娴道。
“是我昨日慌了神,这才,此事怨我……”
严氏自责道。
“我不是责怪母亲的意思,”
吕娴拉住她的手道:“只是母亲实在太过宽仁,治下太松懈,那些下人,嘴上没把门,行动无规矩,竟把家事传的人尽皆知,还添油加醋,让我温侯府沦为笑柄。母亲实在太良善了。对下人们下不了手来管。这才乱糟糟的……”
“娴儿,你既有法,不若管管。”
严氏道。
“其实貂婵可以,她在司徒府上长大,小小的温侯府,对她不在话下,只是怕母亲不肯放权,即使肯放,昨日又把她闹成这样,她心中羞恼,哪里肯出来管,她才貌是有的,手腕也是有的,叫她替母亲来管家事,母亲只管好她便成了,外面人,家里人也只叫母亲好,说她坏的,坏人由她做,最好不过。”
吕娴看严氏没主张的样子,便知她心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