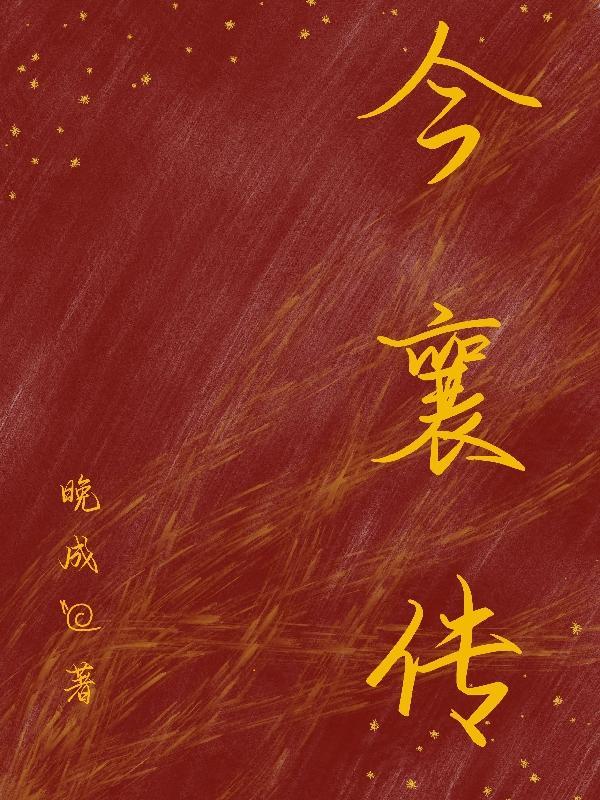搜读>当女博士重生到民国守旧家庭类似的 > 第88页(第1页)
第88页(第1页)
楚望大笑。但是出于替隐瞒真真偷偷参与了葛公馆的宴会这件事,她决定对葛太太三缄其口。
真真后来再没出现在葛公馆的任何场合,故而叶文屿也次次都扑了空,满怀期待而来,却败兴而归。谢弥雅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并一次不落的如实禀明真真。末了,又补充一句:&1dquo;我猜再有一次找不找你,他必定会按捺不住,在你放学回家的路上堵住你表明心迹了。”
真真认真想了想,说:&1dquo;若他真来,那我便答应他。”
弥雅与楚望都有些吃惊。弥雅含着笑问道:&1dquo;你不介意他被我们最讨厌的林二小姐抛弃过?”
真真笑了笑,正色说道:&1dquo;虽然葛太太说&1squo;让他以为这是个美好的误会’,但你我都心知肚明——这就是赤裸裸的勾引。上等的勾引,也是勾引。我勾引他在先,那也是因为我依旧对他存有好感,我无法否认这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昨天你让我去抛头露脸时,我便好好思考过这个问题了:&1squo;我到底还喜不喜欢他?’想明白这个问题,我再告诉自己:若是成功了,那便与他好好在一处处着。若是失败了,大不了再丢一次人罢了。我目的达到了,却将他一脚踹开,只为了满足自己高贵的虚荣心——那么我与林允焉有什么分别?”
尔后,真真又说:&1dquo;倒是你。你这么年轻,你真心愿意与那蒋先生恋爱?你条件好过我,想要挑一个怎样出色的男孩子不成问题?”
谢弥雅笑了笑,不作答,便将这个问题敷衍过去了。
后来某天真真不在的时候,谢弥雅终于肯向楚望剖心掏肺的谈论这个问题。
&1dquo;不肯同她讨论这个问题,只因我嫉妒她。”她笑着说。
&1dquo;我嫉妒她,嫉妒得狂,只因与她比起来,我更觉得自己卑劣。我大好年华,何尝不想像她一样,和一个年轻美好的男孩子,有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呢?横冲直撞,头破血流——可我没有这个资本与底气。我父亲有钱,也敌不过家中姐妹众多。父亲疼爱我,将来也必定会为我置备一份丰厚嫁妆——也许旁人看起来丰厚,但是对于我来说,远远不够。我甚至可以预料到,若我不去争取,我婚姻以后的生活,必然会比出嫁以前低上许多许多个档次。我是个拜金主义者,所以即便有许多好的男孩子追求我,但是除了看他们英俊年轻的面孔与绅士得体的举止,我还得去细细探寻一番——他们是否娶得起我。家世背景差一些的,我直接排除。家世背景雄厚的,家中恐怕未必肯给他置一房杂种正房太太。所以我的选择范围小了许多许多&he11ip;&he11ip;我喜爱金钱带给我的优渥生活,我也清楚的明白为此我要付出的代价。”
&1dquo;何况蒋先生有什么不好?有钱有势,成熟稳重,知情知,还懂得容忍我的许多脾气。葛太太再了解我不过,于她看来,蒋先生于我而言,是个相当不错的归宿,可不是比那幼稚的叶文屿好太多了?”她拨弄着葛太太摆在茶几上的一盆秋海棠,兀自笑了,又笑得有一些不大确定。过了阵,她又问楚望:&1dquo;那么你呢?听真真说,那男孩子为了讨你开心,带了一只巨大的泰迪熊漂洋过海来找你,似乎是一门不错的婚约?那么你爱他么?”
&1dquo;兴许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婚配对象,但是&he11ip;&he11ip;爱情么,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不大懂。”楚望仔细想了想,笑说道。这实乃大实话:上一世宅得太厉害了,闲暇时间都是跟比利小说作伴,故而她从没有得到过什么机会谈恋爱,也更没什么资格跟她讨论这个词。
&1dquo;我觉得你是个非常理智的人,少言寡语,做事却极有目的性,”弥雅说道,&1dquo;可是太过理性,则往往与爱情无关。婚——使一个女人昏了头的事,可不是一件一时兴起的、不计后果的的事?因而我也明白,对于蒋先生,我的目的太过明确,所以那也绝不是爱。那么你呢?”
对于这个问题,楚望其实是无暇考虑的。不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她有别的太多的事情要做,根本没有办法分心来恋爱。太忙——而无暇恋爱。
她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常常喜欢躲在众人背后,以上帝视角看尽百态,偶尔心底会有一番喟叹或者嘲讽。对于大部分的事情,她都十分缺乏参与感,只除了一件事——她的专业知识。她认真投入课业,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往往需要一个极致的、非常简单的环境,让她全身心的,百分之百的投入——结果才能使她百分之一百的满意。
为什么女人一定要有爱情?
从大学时代开始,看尽周围女孩子们为爱人全身心贡献自己,不撞南墙不回头,最终撞得头破血流时,她无数次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男女不能各司其职,在各自领域做到极致,直接步入婚姻殿堂?
爱情不过是进化的主导力量,是一种激素作用。激素导致的好的后果——是为了将基因传递给后代。激素的负面影响——便是使人疯狂而不计后果。
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略过激素的负面作用,直接达到前一种效果?
她当然没法将这一番思考传达给谢弥雅。她的许多思想都没法使人理解,所以在大多数场合下,她都选择缄默。
——
拥有烦恼的,除了葛公馆的女孩们外,也包括徐家的男孩子们。
真真来葛公馆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楚望要带莱昂去徐家学拉丁文的时候。某天,真真将莱昂留在楼下会客厅,悄悄上楼来同楚望说:&1dquo;莱昂最近状态有些&he11ip;&he11ip;古怪。他谁也不肯倾诉,我怕他憋出问题来,你知道么?”
一开始楚望并没有觉察出莱昂的问题,却率先现了徐文钧的古怪。某一天,她在徐宅教拉丁文时,课余时间,她突然听到徐文钧对文妈说了句:&1dquo;duhexe!”(你这悍妇。)
这是一句典型的德语脏话。楚望拉过徐文钧来,义正言辞的问道:&1dquo;这句话是谁教你的?”
文妈就算是个下人,但是好歹也是个长辈,而尊重则是一个有教养家庭长大的孩子应懂得的基本做人道理。少年们第一次接触到脏话,往往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困顿了一阵,说,&1dquo;莱昂教我的。”
楚望则十分困惑不解:乔公馆里只有葡萄牙文、英文与日文的学习环境,他上哪里学来的德文?
没多久,这个幕后罪魁祸,便被她在葛公馆里捉了个正着。
真真照常在没课的周三下午带莱昂来到葛公馆,随后便与弥雅上楼喝茶去了。楚望刚到家,上楼去换衣服,故而莱昂有约莫半小时时间是独自带在楼下会客厅的。
那日她中途突然想起背包落在了会客室。折返回来时,便见比常人都要苍白一些的谢择益与莱昂,两人一大一小的坐在高脚凳上用英文聊天。
谢择益正说道:&1dquo;&he11ip;&he11ip;今天学这一句:dasgehtsiegarninetersheisser!”(轻蔑语气:你这坨小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