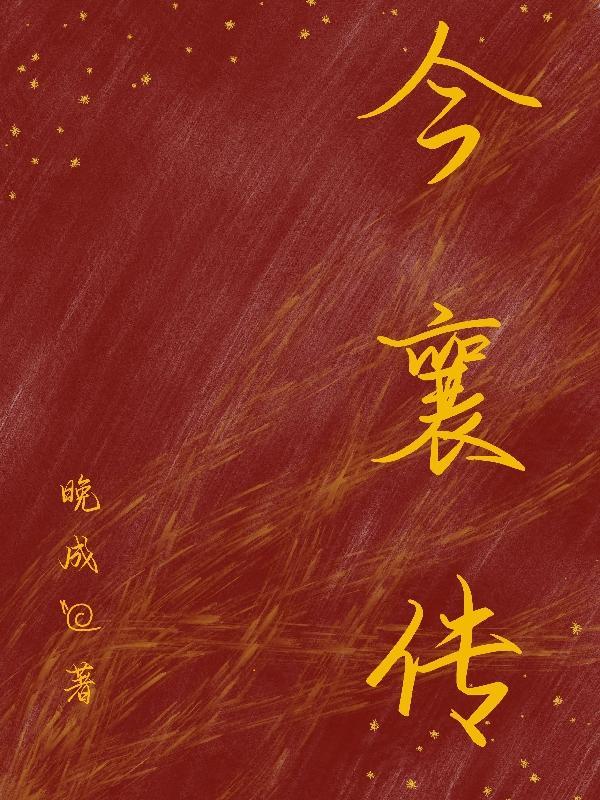搜读>某个郑可心广播剧免费听 > 第201页(第1页)
第201页(第1页)
但每一个都不是许念念,她们没有念念好看。
这一年,郑可心很少会想起许念念,因为忙,因为累,因为不敢。
只那么一次,元旦的时候,郑可心一夜无梦,半夜却忽然惊醒过来,老家的旧床比出租屋的要大上两圈,她一睁眼,灌入两口急促的呼吸,心口顿时落空。
她仿佛溺水濒死总算浮上水面,又仿佛刚从温暖的怀抱中抽离般,迫切的想要抓住什么,全身紧缩攥紧了被角不肯松手,就这样僵持了五分钟,直到身子麻出了绵长的痛感,才后知后觉的明白过来。
下雪了。
今年的初雪踩着年的钟声,来得格外晚,郑可心睡意全无,披了单衣坐到阳台的窗前,睡前的薄雪已经抱了团,落了厚厚一层,郑可心推开窗,用力握了一捧,再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看着融化的雪水顺着衣袖流到地面上。
农村年味很足,一周前就贴好了对联福字,苏瑛玉还买来红纸剪了窗花,吉祥和祝福萦绕在这个变故横生,至今艰难的家里。
春节到,人欢笑,贴窗花,放鞭炮。
郑可心用冻僵的手碰了碰规整的窗花,天边的团星仿佛一朵永不坠落的烟火,南面一朵,北面一朵,越过茫茫夜空,才能看见彼此的轮廓。
郑可心的感情一直克制,情绪一直平稳,然而此刻,毫无征兆的想念却席卷而来,几乎将她淹没。
她只是单纯想念,疯想念,只是一日不见,度日如年。
她记得曾经的年,记得在她家小小的阳台上,收到的最好的年愿望。
记得许念念眉眼弯弯。
也记得许念念说,雪化了就是海,海睡了就是雪。
她觉得自己大概被许念念带走了一部分,她们分开了,视线遥望不及,冷风吹不见底,这辈子就都补不上了。
复读的时光短的可以忽略不计,交完考卷郑可心回头望去,已经找不到太多的回忆了,而后大学如约而至,军训、百团大战、第一次期中考,她越走越远,离曾经的小小出租屋有了漫长的距离。
她愈平和、沉静、每日早起晨练在池边背书,与人自然交谈,报名参加心理学社团,甚至偶尔会加入宿舍活动,和舍友们一起玩剧本杀,扮演一只重生穿越会说人话的大猩猩。
她的大学生活正常、平凡、简单、似乎已经走向了另一段旅程,然而隐晦的想念依旧隐藏于平和的表面之下,让她英语课频繁走神,撞见短女生就急刹车,她也想过办法改正,却都没什么用,仍旧会在乔源问她:“我记得你不是爱吃辣的吗,什么时候爱吃甜的了”
时,下意识回答:“念念爱吃。”
这句话一出,郑可心长久恪守的约束忽然松动,蹩脚自欺的告诫默然离场,许念念已经去了日本,她的想念不必压制,大可以宣之于口,或许感情并非无底洞,她无所顾忌的挥洒,总会有消耗殆尽的那一天。
于是郑可心剔除了所有本就不感兴的娱乐活动,没课的日子吃个煎饼就往乔源工作室跑,每天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和面,做出的面包色香味俱全,种类丰富,她却不怎么吃,只是带到班上分给同学。
室友们起哄:“你这手艺也不知道以后便宜了谁。”
她也不做解释,只是温柔的说:“她的手艺比我好。”
然后迎来善意的起哄声:“咦——男朋友啊。”
郑可心恍然如梦,点了点头。
工作室添置了很多家具,都是郑可心淘来的,小碎花杯一人一个,包括硬汉乔源。
橘子上市的季节十元一袋,约莫二十个果子,用果酱慢慢熬了,可以喝上一周橘子茶。
转眼又是一年年,工作室供了财神爷,宁致闹着要写福字,郑可心思来想去,最后落,乔源凑近了一看,果真是——今天心里很高兴。
他盯着那张写了念字的红纸愁,扭头问宁致说:“有没有啥歪门邪路,例如把这张纸烧了磨成灰对进豆浆里,分七七四十九天喝下去,她俩就能白头偕老,再也不折磨我的那种?”
有了一月后,郑可心不再是孤家寡人,转眼成了个半大孩子妈,孩子长身体,要吃罐头、小鱼干、还要更大的窝,郑可心只好给乔源当小工,帮忙接待客人、布置内景、或是拍摄样片。
刚上手的模特总是僵硬,郑可心面色如水像要出家,在悲伤情绪十足的落叶写了满脸的平和淡然,气的乔源跳脚:“姑奶奶!想想你儿子!罐头要紧!”
然而郑可心的情绪常年压制,实在无法收放自如。
第n次叫停后,被喊来帮忙打光的安冀忽然想起了什么,打开电脑翻出了一个隐秘的文件夹,调出了高中时的历史相册。
往下拉,最后的文件里装着高三末尾,拍摄毕业照的那几天,彼时的她们还是青涩稚嫩的模样,张牙舞爪的,活碰乱跳的,旧相片里装着夕阳下的教学楼,装着一脸怒色的班主任,装着正在挨打的乔源和咬牙切齿的宁致。
宁致把卷子团成桶高高的头顶,眼睛瞪着,头炸了毛,震怒的声音仿佛要穿透相纸和岁月,再训乔源一番。
当然,也装着郑可心和许念念。
隔壁班实验课拖堂,他们班被喊去提前拍摄毕业照,偏偏许念念不知道跑去了哪里,郑可心翻遍了办公室也找不到,只好执拗的守在通往操场的必经之路上,安冀跑回去催她时,刚好看见下楼的许念念从台阶上飞奔下来,扑进郑可心张开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