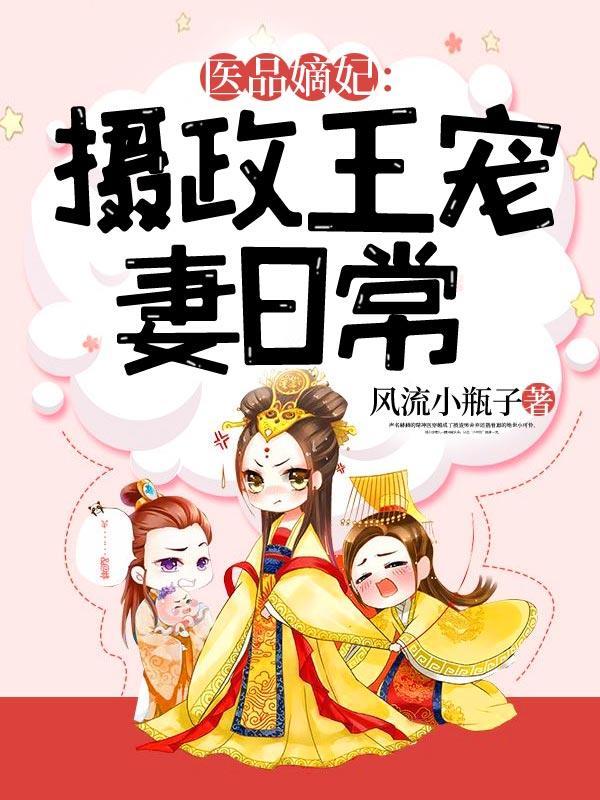搜读>春风吹又生是谁写的 > 第95章(第1页)
第95章(第1页)
陆珘捧起海碗大的汤药,笑眯眯道:“夫君,你会骗我吗?”
“阿珘,我对你一直都是坦诚的。”
谢徽止取出帕子温柔替她擦拭唇边残存药渍,“慢点喝,也不怕烫。”
她晤了一声,深吸口气,接着又扬头咕咚咕咚喝药:“这药苦,冷了更难咽,而且红袖说了,这是治我失忆的,夫君对我这么好,我得快点想起来好报答夫君。”
谢徽止平稳地笑了笑,揽紧她瘦弱的肩:“你我夫妻了,谈了什么报答不报答。”
凤求凰
是夜风清月明,星野低垂,崔叙放下公文回来,陆珘已经在侍女服侍下朦朦胧胧睡过去了。
睡着了的她眉目安然,睫毛纤长,鼻头微皱,喷出浅浅的温热呼吸,浑然不觉在枕上留下一团小小的洇痕。
几乎乖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金丝楠木的拔步床上是一对戏水鸳鸯枕,她睡里头一只,那外头那只自然是给自己留的。
也许是坠崖时的惊恐犹未从潜意识里消退,又或是他上榻动静过大惊扰了她,总之崔叙躺下没多久,陆珘便发出黏人的哼唧声,微微侧身她在一片灯烛俱灭中睁眼,此时恰好屋内清月透过窗轩入户,照亮崔叙高挺的鼻梁。
夫君挨她极近,只需一伸指尖便触手可及陆珘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心头突然泛起一丝甜意。
他并没有醒,似乎是太过疲惫,这也难怪,还记得白日见他的第一眼,真真是狼狈的让她心疼,听红袖说,自从夫君知晓自己坠入山崖便没日没夜亲自带人深入崖底一寸一寸寻她。
所有人都说地势天险她一个柔弱女子掉下万丈深渊不是粉身碎骨尸骨无存,就是被飞禽走兽吃了干净,是夫君一意孤行不肯放弃,执意活见人,死见尸,这才给了她一线生机。
故而虽说睁眼醒来记忆全无,可老天白赏她这样一位有情有义,不离不弃的俊俏夫婿,却也不算薄待。
却不知自己当初怎么想的,只因子嗣艰难便决心舍下这般佳婿,莫不是被猪油蒙了心?到底是自己亏欠他在先,如今老天爷既给她重来一次的机会,待自己身体调养好了,定要收拾好失忆后彷徨迷茫的心境,踏踏实实尽一个妻子的本分,替夫君遍访名医最后再努力一把,还望那时夫君莫要讳疾忌医才好。
想到这里,陆珘觉得脸颊突然滚烫起来,慢慢伸手摸向崔叙,悄悄十指相扣。
还是尽快熟悉接纳夫君为妙,方可不辜负他对自己的情深义重。
当陆珘挨着崔叙闭眼甜甜睡过去后,谢徽止终于睁开眼,借着月光他缓缓转过头去,近在咫尺就是一个桃之夭夭的绝美女子,长发如瀑泻在枕上,气息绵长,摩挲着手中娇嫩玉手,他情不自禁紧了紧双臂,小心翼翼把脸埋入她的颈窝中。
阿舟,即使是是假的,我也盼你一直骗下去。
愿千帆过尽,你我余生共度。
可惜夫君前半夜睡相规距从容,后半夜便不甚得体,手长脚长恨不能将人勒死在怀里,夜里热醒好几次,手脚并用也推不开,害得她只好认命张嘴大口呼吸,婚后两载还能如此黏人,倒是让陆珘生出些无福消受的甘之如饴。
晨起时,两人四目相对倒是透着些诡异,一个神清气爽,精神奕奕,另一个却萎靡不振的可怜。
崔叙俊眉微蹙,瞧着陆珘一双凤眼里清晰可见的血丝:“夫人昨夜可是未睡安稳,瞧你眼下这青黑,为夫看了甚是心疼。”
陆珘却是有苦说不出,只能生受着,安慰自己是他的妻,习惯就好:“呵呵,还好,还好吧。”
不过窝在榻上,看自家夫君即使身着亵衣,亦如着儒衫般优雅从容净面漱口,倒是打心眼里生出几分赏心悦目之感。
待到各自梳洗完毕,两人坐在窗下喝粥,门窗大敞,正对着朝阳举案齐眉,崔叙举止文雅,陆珘吃相亦是秀气,虽举箸无声食之无言,却是异常和谐。
夫妻两人用完粥点,他道:“郎中说你如今不宜舟车劳顿,我已告了假,这些时日就陪你在豫州养伤,夫人可有什么想做的。”
陆珘闻言唇角已染上笑意:“原想替夫君绣块汗巾帕子,只是我现在手边提不起力气,不如夫君就弹琴给我听罢。”
说话间她已然倚在软榻上,手肘随意搁在小几上,腕间新伤迭着旧伤酸胀发软,脑袋斜倚在软枕上,昨夜本就未睡好,如今吃饱喝足,更觉困顿乏力,现在只想懒洋洋瘫着等人伺候。
崔叙也不介意被她像长工一般使唤:“想听曲子倒是无妨,只是答应我的帕子,待你伤好了却不能拖延。”
陆珘歪着脑袋,漫不经心打了个哈欠:“难道从前我就未给你绣过吗?怎一条帕子你还怕我抵赖不成。”
“你我从前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故而你对我也不甚上心,如今难得你主动提起,我自然不能错过。”
崔叙顿了顿难掩落寞,这才强打起精神嫣然一笑,“嗯,想听什么曲子?”
“唔,都行,我如今也记不清曲名了。”
陆珘笑容勉强,打量眼前温润无辜的男人,深觉自己从前亏待他了,同时心中暗下决心,从明日就开始动针,绣个百八十条,且条条不重样才好,方可弥补自家夫君受伤的弱小心灵。
红袖熟练焚香,崔叙修长的指尖轻轻拨动琴弦,清幽缠绵的曲调便行云流水从弦上倾泻而来,缓缓在空气中回荡。
陆珘轻轻阖眼,懒洋洋跟着曲调默默打了个哈欠,平心而论夫君技艺极佳,甚至谦虚一点可谓高超,只可惜她于音律一艺上着实涉猎不多,只分得清好听不好听,即使再妙的曲子在她耳里也无异于牛嚼牡丹囫囵吞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