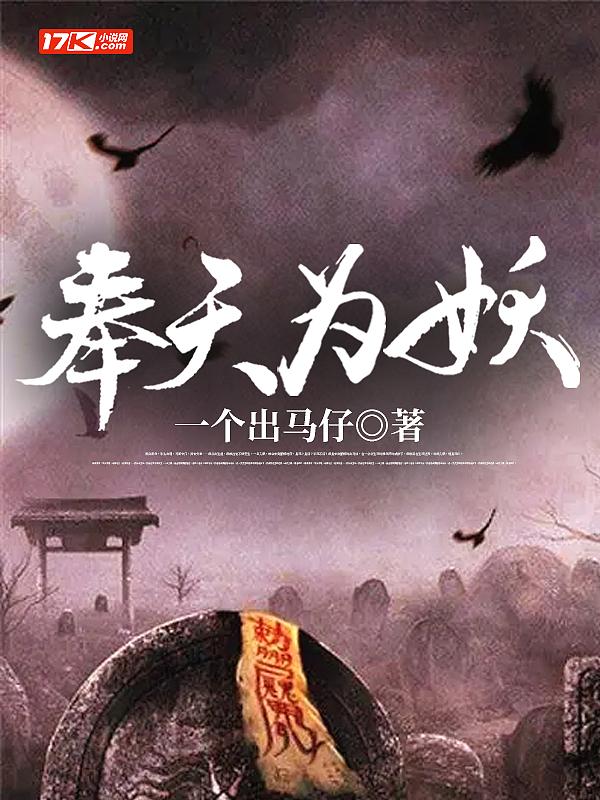搜读>山巫山 > 第48章(第1页)
第48章(第1页)
门外,一直偷听的乔四海眼圈泛红,捂住嘴巴,无声地哽咽,悄悄离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想到刚才听到花信的哭声,他一颗心揪着,难过得不行。原来,你竟有这般曲折的身世吗?甚至,还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哥,你是不是人又怎样呢?反正你永远是我哥。乔四海头埋在枕头里,利落地擦去眼角的泪水。
“嗨,怎么搞得跟综艺节目似的,大家还卖起惨了呢。”
殷楚风生硬地岔开话题,作为在场唯一算是‘正常人’的他,羞愧难当,此刻竟生了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好像,他不变点态,就没有办法融入进去似的。唉,都怪自己太普通太平常了。殷楚风自责。
“行了,大家别想这些了,人生匆匆忙忙,不过百十年,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殷楚风讪笑,底气不足,毕竟他作为‘正常人’,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难免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嫌疑。
一计不成,殷楚风又生二计,“对了,我一直好奇呢,你说昨晚,为什么木偶放出了乔四海身体里的邪祟,他们两个没有联手呢?它俩要是合作了,估计应该没咱们啥事了吧。”
你们也用不着在这里哭哭啼啼了。殷楚风心中暗暗补了一句。
花信认真思考,须臾后回道:“我想,除了火羯报复心强这个特点,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大概邪祟之间也是论资排辈,等级森严吧,好歹火羯活了几百年,木偶不过才二十多年,一个小辈居然把长辈指使得团团转,火羯把这当成了挑衅,气不过才想除了它吧。”
“这不对啊,”
殷楚风觉得花信的道理有些毛病,“那个郑信子,死了也不过二十多年吧,她也算是后辈,怎么就能对火羯出言不逊呢?”
哪壶不开提哪壶,殷楚风后知后觉噤声,用余光偷瞄花信,注意到他脸色没变,才松了口气。
“是啊,为什么呢?”
花信纳闷。
“也许,邪祟之间更靠实力说话,”
林岳提出自己的见解,“火羯能打过木偶,所以硬气;但是打不过郑信子,只能落荒而逃。”
有道理。花信和殷楚风默契对视。
“那个,我能不能说句话啊。”
听完他们的争论,默不作声的林岚开口道,“郑信子不过也二十几年,她又没害过人,怎么就能打败火羯呢?”
一个小问题,把三个人都整沉默了。是啊,当时,火羯害了十几人,力量达到顶峰,郑信子是怎么打败火羯的?
“哎呀,想这么多干嘛?反正它帮咱们解决了木偶,虽然说是阴差阳错,但也正好省了咱们不少力气。快十一点了,各自回屋去睡吧,明天不是还要去泰宁溪找水鬼吗?”
一到动脑的时候,殷楚风变得格外烦躁,他打了个哈欠,立刻开始赶人。
回到房间,屋里漆黑,估摸着乔四海已经睡了,花信蹑手蹑脚踱到自己的床边,刚躺下,对面的乔四海像立军令状似的说道:“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抵制住邪祟对我的控制,不让它伤害你们。”
“好。”
黑暗中,花信泛起了笑意。
清朗的月色,沉静,安稳。大俞山脚下,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突兀地立在地上,石碑上刻着十六个大字,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一男双姝,方解此道。
风禾坐在石碑上,欢脱地望向大俞山,大声呼喊,“小白,你放心,我已经找到救你的办法了,你再等等我,好不好。”
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然而,并没有人回答她。风禾不以为意,幽幽唱起了古老的歌谣,“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花信,你们可要快点来哦。闭上眼,风禾笑得纯真,身上逐渐发出白色的光芒。
夜里,乔四海迷迷糊糊做了一场梦。在梦里,他置身于漫无边际的黑暗中,一直有道声音和他说话,那声音极具蛊惑人心的力量。
“乔峻?乔峻?”
“不,我是乔四海。”
乔四海回应道。
“不,你就是乔峻。乔四海只是你觉得自己孤苦伶仃,自甘堕落的一个化名罢了。可是乔峻,这个名字是爱你的爷爷和奶奶为你取的。乔峻,难道你不想他们吗?你的爷爷,奶奶。”
那道声音谆谆善诱,接着,一男一女两个老人凭空冒了出来,乔四海看到他们,难以置信,“爷爷,奶奶。”
乔四海的爷爷奶奶并未说话,只是和蔼可亲地看着他笑。不对,爷爷奶奶早就去世了,这是?
“你是那个邪祟。”
乔四海恍然大悟。
“是啊,我就是。”
噌地,一个纸片人飞到他眼前,“你说我是邪祟,可你身边的人更恐怖不是吗?他一出生就死了,偏偏有个女人的灵魂为他续命,你知道死人续命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就是个似鬼非鬼的怪物。”
“我不准,”
乔四海勃然大怒,挥拳捶向纸人,“我不准你这么说他。”
纸人灵巧地躲过,“嘻嘻,你不准我说,难道就能掩盖那男人是个怪物的事实了吗?”
乔四海捂住耳朵,竭力忽视那道声音,“我不听,我不听,你给我滚。”
“乔峻,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你,你太可怜了。不如,你摘下脖子上的玉佩,我让你和爷爷奶奶团聚好不好?还有你的爸爸,妈妈,你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吗,这样,你们一家永享天伦之乐好不好。”
邪祟继续蛊惑。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
乔四海发出冷笑,“你想占据我的身体,让我受你控制。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