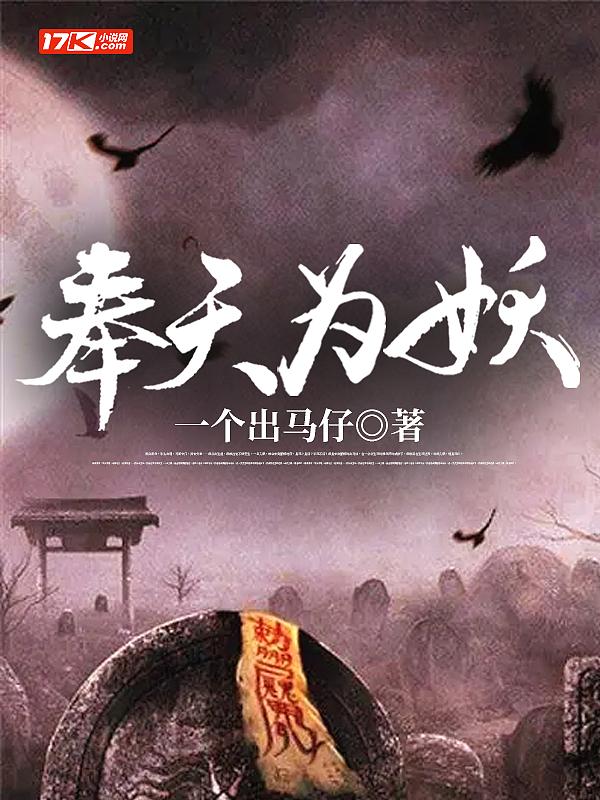搜读>在吃旋转小火锅 > 第 43 章 不懂得轻重之分(第3页)
第 43 章 不懂得轻重之分(第3页)
在她强硬又急切的动作里,娄与征看得出她憋了很久。
她和他一样,都随着分开把汹涌的欲望压在看不到的地方,一压就是五年。
“娄与征,我喝多了。”
明雀躺在沙发里,溢过生理泪水的双眸还红着,显得楚楚可怜。
可偏偏又一边可怜兮兮,一遍又伸出手去向——
她说:“我喝多了耍酒疯,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可以把所有过错都扣在我头上。”
无形之间的允许和邀请,他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怎么会听不懂。
窗外雨雪漫天,方才在卧室他用手帮她倾泄过一次之后,自己早已紧绷到崩溃边缘。
身体里仿佛有一座火山,岩浆充斥到他每根虬起的青筋之中,炙热鼓胀着,试图破土而出。
娄与征睨着她,视线难以从明雀身上挪开。
释放过一次的女孩浑身发了层汗,清洗过后脸颊仍然留有未落的潮红,双颊粉白夺目,吹弹可破。
她裹着毯子,扬着一双渴求又羞怯的杏眼,目光盛满了他。
呼吸已然沉重到了极致,手指痒得止不住弹动。
下一秒就要克制不住了,娄与征猛地捞起毯子把她整个盖住,不能发泄的□□化为愠气从嘴里威胁出来:“给我老实闭眼睡觉。”
“别惹我发火。”
说
完他头也不回转身回到卧室收拾床单。
被子里的女孩还在支支吾吾,殊不知这场勾引与对峙中……
娄与征站在衣柜前,往下看了眼,阖眼深呼。
狼狈的是他。
…………
床单和被罩都塞进了洗衣机,适量比平时更多一点的洗衣液进入稀释盒,他弯腰按下了洗衣机开始的按键。
全程四十五分钟。
娄与征站在卫生间里,看了眼紧闭的门,又看了眼嗡嗡运作发出噪音的洗衣机。
环境与声音越单一,就越是难以将注意力转移出去。
眼前没了明雀,他身体里的躁动却没有丝毫平息。
半晌,娄与征叹气,把卫生间的门反锁,单手撑着墙壁,低头拉开压抑着火山运动的云幕。
…………
洗衣机的运作已然快要过去四分之三的时间,嗡嗡震动,甩干着衣物。
啪嗒,一滴汗从男人额头滴到盥洗盆上。
娄与征皱紧了眉,撑着台沿的手臂爆着青筋,透着亟待抒发的男性荷尔蒙。
不管怎么……都难以抵达最后。
他瞥了眼马上就要洗完的被单。
略微弄到疼而折起的眉宇渡上烦躁。
就在如何都抒发不了的时候,娄与征耳畔响起方才女生柔软又沙哑的那句——
“我喝多了,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可以把所有过错都扣在我头上。”
他恍然停了手,撑着盥洗盆呼吸急促。
娄与征盯着挂在一侧的粉色小毛巾,眼神沉下去,做出了某种决定。
明雀,要怪也都怪你。
…………
他走出卫生间,果然如预料的,明雀躺在沙发床里已经睡熟了。
男人踩着地板,脚步沉重却也悄声,宽大的身影逐渐染到她身上。
娄与征在她头顶的位置坐下,盯着她呼吸平稳的酣睡模样,气不打一处来。
起居室里寂静了很久,洗衣机马上就要收起转动的声音。
他抬手,缓缓牵起了她柔软的小手,指腹搓弄几下,略有用力。
娄与征睨着她,视线从额头一路流连到鼻尖,唇瓣。
他轻轻开口,哑声性感:“小鸟,你说的,不管发生什么都是你的错。”
“我帮你那么多,你也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