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读>险道神在线阅读 > 2第2章(第1页)
2第2章(第1页)
只有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山寨兄弟情,亲当然是不会亲。
关捷的嘴伤不严重,就是落地的时候来不及抬头,自己给自己啃破了内黏膜,这地方筋和血管多,所以血才流得凶,肿得也夸张。
五官稍微动一动,给人的感觉就会大不相同,路荣行越看越觉得他这刚出炉的翘嘴巴蠢出了喜感,忍着笑问他:“疼不疼?”
关捷正垂着眼睛往下看,目光越过鼻尖就能看见那片肿起来的嘴,不照镜子他都知道自己现在肯定丑爆了。
路荣行的笑容无疑是一种二次打击,这让他忽然自卑起来:“不疼,这肿什么时候能消啊?”
路荣行从小中规中矩,受伤的经验不够丰富,只能瞎猜一气:“小半天吧。”
关捷一听那还得了,跑去漱口的时候都是一路低着头。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小女生围着他笑嘻嘻,但作为一个至今还误以为太阳和月亮是绕着他在打转的小屁孩,关捷自有一个属于无知少年的偶像包袱。
在他奔往水龙头的路上,路荣行半道直接回了教室,捡起扫把继续值日。
五分钟之后关捷折回来,在六年二班的教室门口探了下头,一眼没扫见路荣行的人影,但是听见他和张一叶正在说升学和六一表演的事。
关捷心里霎时就想,路荣行总是忙的,不像他这么闲……念及此他身体往门框上一撞,借着那点反弹力将自己像个肥皂泡一样给弹走了。
他离开教学楼,在学校有且只有一条的主干道上走了没几步,宿命一样地碰到了校长。
校长姓马,是个笑起来就像弥勒佛的高胖子,习惯每天放学都巡逻一遍校园,看看有没有熊孩子翻墙打洞和聚众斗殴,和每天放了学都不立刻回家的关捷特别有缘,从小相逢到大,已经认识他了。
“小胡子先生又才放学啊,嗯?嘴怎么肿成这样了?”
关捷不是很喜欢这个历史悠久的绰号。
他刚开始学习写字那会儿掌握不好力道,来上学的全部任务就是将铅笔摁断了再削,那时候镇上的文具店里还没有转笔刀,他只能用小刀刮,刮完了指头上全是黑末,爱蹭鼻子的坏习惯让他嘴巴上面总是有两撇或一瞥胡子样的黑印子。
校长好几次碰见他都这样,就胡子胡子地叫了起来。
关捷现在已经不留“胡子”
了,不过他还在怵老师的年纪上,不敢怒也不敢言,只敢老实地立正站好,脸朝着地面努力地扯淡:“校长好,嘴这个,是我自己摔的,校长再见。”
校长不知道单杆冲突事件,乐呵呵地说:“好好好,玩的时候注意点,回家去吧。”
关捷将装满弹珠、碎碗底和画片儿的沉重书包往肩上一颠,走着走着就开始小跑,心里想的是玩屁啊玩,他都快没有伴了。
荔南镇小门口有条河,学生们所有关于水中生物的知识都来自于它,河上架着座短桥,卖烧烤和麦芽糖的贩子常年在走人的道上驻扎,一左一右像两个护法。
关捷嗜甜怕辣,爱屋及乌每次都要走麦芽糖那边。
敲糖的老头大概是看出他没有钱,抽着卷烟也不冲他吆喝,关捷从盖着蒸屉布的糖篓子前面经过的时候心里有一点点后悔,觉得他应该等路荣行一起走。
路荣行是多大一个款他不太清楚,他只知道这位兄弟去买辅导书和琴弦从来不用问父母伸手要钱,不像他这种小可怜,一分一厘都来自于死乞白赖。
不过走都走了,他是不会回头的。
而且路荣行不爱跟他一起玩儿,关捷觉得那就这样吧。
只是话是这么说,在单方面冷战的这几天里关捷还是挺失落的,像是文具店里又多了一个他买不起却又贼惦记的昂贵玩具。
他朝河里踢了两颗鸟蛋大的石子,右拐左拐再过个路口,麻雀大小但人满为患的游戏厅就出现在了眼前。
如果说能为大人浇愁的是麻将和酒,那游戏无疑就是小孩的忘忧草,关捷一头扎进去,很快就被劲爆的打斗鼓舞得忘记了路荣行是哪根葱。
……
隔壁那根葱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是六点半,天还没暗,不过来自于阳光的清晰视野已经开始消退。
远处的田野里能看见不断升高的火光,那是堆起来焚烧的油菜杆,就地烧过后将灰挑开,能省去很多搬运和堆放的工作,种地的人喜欢这么干,但是路荣行不喜欢。
这时的他还不懂这种收播方式和环境恶化之间的复杂联系,只是纯粹因为有慢性支气管,而对这种扰得他咳起来没完的扬灰深恶痛绝。
不过很多年后,每当他想起这种升腾在广阔平原上的巨大火炬,心中都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类似于“希望”
和“自由”
的感觉,因为城市的空间太逼仄了。
然而正当此时他体会不到,只是顿住脚,单跨起书包从兜里掏出了一个作用聊胜于无的口罩。
就这一低又一抬的时间里,关捷就凭空冒了出来,路荣行看见他猫着腰从游戏厅溜出来,双手背在身后捂着书包,跑成了一只逃命的兔子。
而在他刚刚跑开的游戏厅门口,相继挤出来三个年纪大一些、痞里痞气的少年,他们追着关捷跑了一小段之后停下来,改为抬起胳膊用食指戳着他放狠话。
内容十分俗套,掐掉脏话之后剩下的硬核不多,就说以后见关捷一次打他一次,不打自己是他孙子。
关捷充耳不闻地往前跑,跑出老远了才慢下来,在走动间掉了个个儿,脆生生地骂对方是贼不要脸。
路荣行这时刚好隔着马路,站在那三个少年的斜对面,这阵对骂他听得一清二楚。
他不是很清楚这个贼的含义,只看见他们被激怒了,但又舍不得离开游戏厅,骂骂咧咧地钻了回去。
关捷不瞎,比完中指就瞥见了路荣行,不过他假装没有自己没有看见,旋即转过身,从路边的杂草里摘了根狗尾巴草,抽抽打打地往前走。
走了两米远他就有点想回头,不过还是忍住了。
这时两人相距大概有个三十来米,能看见人但是看不清表情,路荣行宽以待人,以为他是没看见自己,就抬高音量喊了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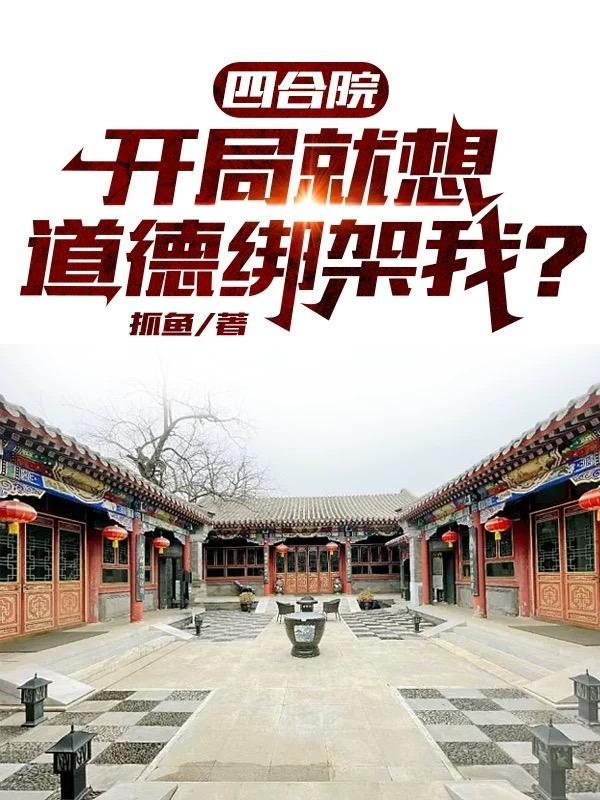
![[演艺圈]死灰不复燃](/img/3200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