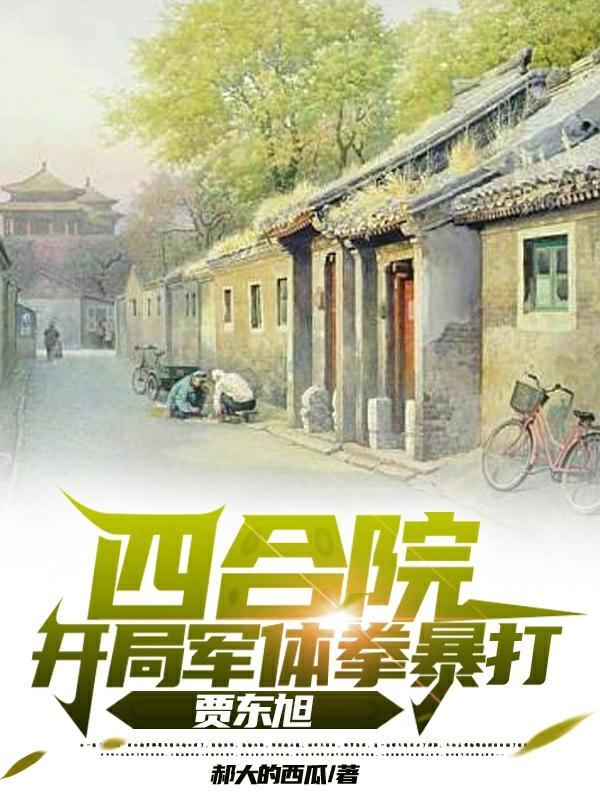搜读>公主病和爬山哥是谁 > 第2頁(第1页)
第2頁(第1页)
倪雪的視線在上面停留了一秒鐘。
這還是倪雪第一次見到蔣冬河沒有穿校服的樣子。
儘管明雅從來沒評定過那些雜七雜八的名號,但只要是個有眼睛的人看見蔣冬河,就會在內心給出答案:這人一定是我們學校的校草。
對此,倪雪自然很不服氣——從來都是他擁有別人沒有的東西,哪怕只是學生口中流傳的一個稱號,也沒有他得不到的道理。
可惜事與願違。
他從小就被長輩說長得像洋娃娃,直到現在去市買東西還會被收銀員夸「這小孩長得真漂亮,像混血」,看他不順眼的同學背地裡會叫他小白臉,跟蔣冬河收到的評價南轅北轍。
蔣冬河在桌面一摞文件中翻找片刻,遞過來一個紅色信封,「給,這是你的錄取通知書。」
相比之下,蔣冬河的態度顯得十分自然,他語氣平靜地說:「好巧,以後還是校友。」
「……嗯。」倪雪勉強擠出一個音節算是回應,接過信封后轉頭走人。他一點也不想在這所學校里過多停留,尤其不願與蔣冬河再有什麼交集。
蔣冬河只是在陳述一個客觀事實,倪雪卻無端覺出了幾分嘲諷的意味。
事到如今,蔣冬河依然是人們心中的高考狀元,明雅校草,倍受愛戴的十班班長,而他卻淪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任誰都能踩上一腳。
不過他和蔣冬河不在同個專業,以後可能也不會再見了吧。
室外的陽光依舊曬得人眼前發暈,倪雪向校門外走,衣兜里的手機同時振動了一下,他掏出來一看,是周延發的消息。
[周延:今天中午吃披薩可以麼?還是上回那兩種口味,可以的話我就點外賣了啊。]
倪雪單手打字,簡短地回覆:[嗯。]
周延是倪雪的初中同學,高中沒在明雅念書,兩人一直是微信好友,但不太熟。能再次和周延產生交集,倪雪其實也很意外。
這還要從他父母出事說起。變故發生後,家中財產全部充當賠償,倪雪幾乎要淪落街頭。於是他聯繫了幾位平時一起玩的朋友,問能不能在對方那裡暫住。
倪雪平時對朋友一詞沒什麼概念,一起吃飯打遊戲的人都可以被歸到這個範疇,現在一想,可能叫「酒肉朋友」「狐朋狗友」更恰當。
如果按照序號排,跟他玩得不錯的狐朋狗友有五位,倪雪先問了前兩個,二人態度如出一轍,支支吾吾閃爍其詞,擺明了不想和現在的他有過多聯繫。
曾經「仗義」的朋友,如今也散得一乾二淨。
周延就是這個時候冒出來的。他主動給倪雪發微信,沒提倪雪家裡的事,而是說兩人作為老同學已經好久不聯繫,不如趁著高考結束出來聚一聚。
再後來,周延邀請倪雪來自己家裡做客,又說他爸媽最近請年假出國旅行,想在這留宿也可以。
一來二去,倪雪就在這住下了。
起初,他沒覺得有什麼奇怪的,以前也不是沒有同學在他家住過,所以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周延的邀請。
在周延這裡的日子還算舒心,他一直住客房,每天睡到自然醒,隨便吃點外賣,再打遊戲到深夜,整個假期過得渾渾噩噩。
除此之外,周延的性格也不討嫌,甚至稱得上貼心——關心和照顧是倪雪以前最不缺少的東西,以至於他根本意識不到,在這種時候湊上來關心他的人反而比較蹊蹺。
某天晚上,兩人如常坐在沙發上聯機打遊戲,茶几上散落著幾個外賣盒,還有兩罐喝到一半的汽水。
一局結束,倪雪拿起其中一罐汽水喝了幾口,就在這時,頭頂吊燈閃爍一下,倏地暗了下去,整個房間頓時陷入漆黑。
人難免會對突如其來的黑暗產生恐懼,倪雪握著易拉罐的手一抖,耳邊響起周延的聲音:「別怕,只是停電了,我一會出去看看。」
倪雪點點頭,而後意識到對方也看不到,才開口道:「那好吧。」
他把易拉罐放回茶几上,重窩進沙發里,聽見周延忽然問他:「倪雪,你之後打算怎麼辦?」
電源被切斷後,平時那些娛樂活動全部無法進行,一股空虛感油然而生。倪雪並非不清楚他的所作所為是在逃避現實——之後怎麼辦?他也沒想過。
周延又說:「倪雪,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考慮什麼?」
黑暗中,倪雪覺察到有人緩緩逼近,下一秒,一隻手攥住了他的腳踝。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對方的咬字比平時更輕緩,「考慮一下和我交往。」
「喂,你開什麼玩笑……」倪雪一驚,本能地掙脫開,一片漆黑中看不見周圍事物,踢到了茶几上的易拉罐,汽水瞬間溢出來,灑了滿地。
「我沒在開玩笑啊,」周延像是笑了一聲,「初中的時候我就能感受到,我們是一類人,你也喜歡男的對吧?而且我們的大學在同一個城市,我們還是可以搬出來一起住,就像現在這樣,不好嗎?」
周延繼續靠近,溫熱的氣息似有似無,倪雪猛地推開他,跳下沙發,「你發什麼神經?」
但倪雪沒有反駁周延的前半句話。
「我一直很喜歡你,你根本沒發現吧?也對,以前你哪裡能注意到我呢……」
喃喃低語仍在持續,倪雪只感覺太陽穴突突地跳,後背上浮出一層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