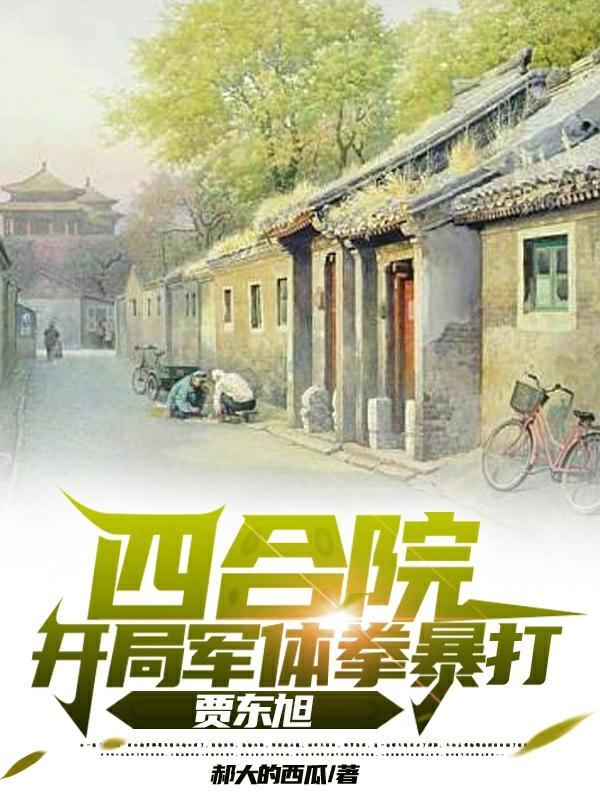搜读>枭鸢 TXT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欸你……”
易鸣鸢欲言又止,沉默瞭一会后说,“茶是用来品的,裡面的茶叶不能吃,隻用来泡。”
“我们这的咸奶茶就能吃,裡面还有牛肉,果干和炒米。”
程枭反驳道。
易鸣鸢难以接受,“甜牛乳也就罢瞭,咸奶茶又是什么?”
正小小拌著嘴,突然毡帐外传来一声清冽的声响。
“公主,奴伺候您梳洗吧。”
莽夫
黎妍好不容易得到接近易鸣鸢的机会,一大清早就来到帐外站著瞭。
有瞭那二十个士兵轮流值守,再也无人敢往她们这些大邺来的奴隶毡帐旁路过,纷纷避而远之。
其实她昨晚说瞭谎,匈奴的男人们虽然从不掩饰他们好奇的目光,常常对她们肆无忌惮的上下打量细看,但根本没人钻进来乱摸。
程枭麾下,转日阙内治军严明,出征在外时向来禁止奸杀淫掠,被抓到不仅会被剁掉手指,受烙铁之刑,还要负责清理整整一年的羊屎牛粪。
喊完那一嗓子后,黎妍惊魂未定地拍瞭拍自己的胸口,她千算万算,没算到这和亲公主胆子大成这样,在人人茹毛饮血的地界,竟还敢背著服休单于偷情。
原先她的计划是趁著易鸣鸢出门的时候,以匈奴男人试图强迫为由,让她把自己认下,作为贴身婢女带在身边,没想到昨晚跟在她身边的不是服休单于,而是另一个发丝微卷的异族男人!
他也许是服休单于派给易鸣鸢的护卫,也有可能是一个大臣,但无论如何,他都不是和亲公主名正言顺的夫君。
那一刻当真惊险无比,被那个瘦瘪的黑脸男人抓住时,她差点以为要死在当场瞭。
黎妍紧盯易鸣鸢数月,和亲队伍刚出发,她就有意无意的想接近这位和亲公主,谁知路上这段时日裡,易鸣鸢不是在抹著眼泪追思亡故的亲人,就是在神游天外,除非必要绝不多说半个字。
为此,她屡试不成,恨得几乎咬碎一口银牙,终于在婚仪后的第二日抓住时机出声让她记住瞭自己,一步步走到她身边。
现在,她的帐子离转日阙最中央的王帐不过百米,某些事做起来易如反掌。
这样想著,黎妍嘴角牵起一抹笑意。
帐内
关于茶汤应该如何饮用的争论被声音打断,易鸣鸢有些意外地皱起瞭细节眉。
她不需要人贴身伺候,答应那个女奴也隻是为瞭达到庇佑她的目的。
当初被恩准小住庸山关的时候不允许带婢女仆从,大将军府隻有些年龄尚小的士兵,尽是男子。
因此在那裡她穿衣佈菜亲历亲为,回去后也没改掉这个习惯。
父兄叛国的消息甫一传出,便有几百禁军闯入傢中,把奴仆和所有御赐之物全都搜刮充缴,她自小一同长大的婢女靛颏也被扣上铁链从她身旁硬生生拖走,卖到瞭澧北,至今下落不明。
易鸣鸢不愿让来历不明的人近身,更何况,这女奴扑在她身前的时候,借著月色能看出她相貌周正,牙齿整齐,手指也修长细软。
在采买奴仆的时候,首先就要看他们的牙齿,因为能最直接的看出奴仆健全与否。
还有手指,若在寒冬腊月裡浆洗做工,不出三年,手指定会粗肿发红。
皮肤和肥瘦在短期内很容易就能改变,可是牙齿和手指分明暗示著这个女奴先前过著养尊处优的生活。
通常这类人有两种可能,傢裡遭瞭事被充作奴隶,正巧被放到瞭和亲队伍裡,不然……就是受人指使,特意被塞瞭过来。
若是遭瞭难的千金小姐,恐怕每日怨声载道的可能性更大,必定不会这样好整以暇的出现在帐外,扬言要伺候她梳洗。
从被哭声吸引,到昨日救下这个女奴,易鸣鸢未曾放下过一丝警惕之心。
她又饮下一口澄亮的茶汤,细细感受喉口回泛过来的清润,当下有瞭决断,对身旁翻著肉干打算给她做一杯纯正咸奶茶证明一番的人说:“走吧,出去以后你先别说话,看我眼色行事。”
“好。”
一如前几日,程枭给易鸣鸢戴好额饰,这东西结构特殊,戴不好容易挂到头发,易鸣鸢尝试过几次但以失败告终后,这份差事自然而然落到瞭他手中。
对于做出窥探行为的女奴,他的印象并不好,若是他的兵做出这样的事,一刀插在眼睛上都算是心慈手软瞭。
程枭不笑的时候面容冷酷,加上异于常人的体型和宽阔背肌,一站出去就令黎妍两股颤颤,抖著声线行礼:“公主安好,公子安好。”
这男人怎么从王帐裡出来瞭!
黎妍听不懂匈奴语,这两天她观察下来,匈奴人阶级分明,住处越靠近部落中央,地位越高,此处乃是最华丽的毡帐,在其馀毡帐都质朴简单的情况下,这个帐子顶部嵌瞭宝石做装饰,还画上瞭鹰的图腾,无疑是服休单于的毡帐。
她小心地打量程枭,他的长相和年龄确实与传闻中的服休单于大相径庭。
“本公主已外嫁匈奴,你该唤达塞儿阏氏,”
易鸣鸢目光往黎妍那裡扫去,淡淡道:“大单于不喜欢被称为公子,既然以后要在这裡久居,你也应当守这儿的规矩才是。”
听程枭说,服休单于要去整治西方动乱的小部落,所以盟约一经盖章,便带著扎那颜他们离开瞭,族内事务交由他暂管。
所以现在整个转日阙以程枭为尊,无人擅言指出易鸣鸢话中的错误。
倒是身旁的人被歪曲瞭身份,带著醋意的大手伸过来,从背后掐瞭一把她的腰间软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