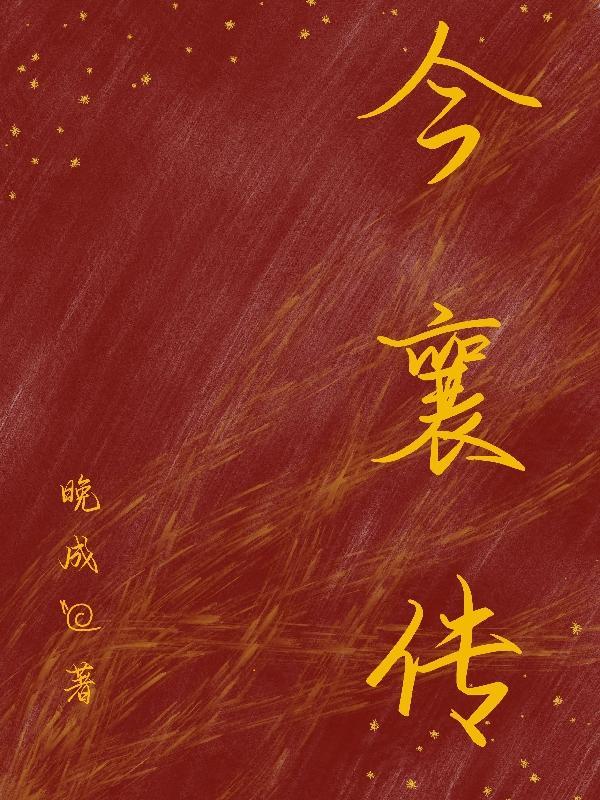搜读>夫郎家的小娇夫最新章节更新 > 第8章(第1页)
第8章(第1页)
苏谷现在是真被惹出了火气,眼神狠戾:“先前说的好好的,这人要落到我的户籍上做我上门婿,如今可倒好,婚契写的含含糊糊,连嫁娶双方都没写明白,难道不是沖着欺负我不识字的心思来的?”
苏桩子匆忙赶来正好看到了苏谷如今的模样,他怔愣在原地不敢上前:“谷哥儿……”
苏谷假装看不见他,态度更强硬:“让我成亲也可以,婚契上得明明白白写着这人必须入赘到我门上来,那两亩田明天我就要耕种,还有说好的新衣我也不要了,直接折合成铜板,一百文一文都不能少。”
“你着哥儿真不要脸,哪有好人家的哥儿当衆给自己争嫁妆的?”
村长做主的婚事还要往外再搭钱,村里人可不干了,有那脾气急的嘴里不干不净的嚷嚷起来,还沖着苏谷挥拳头,想要教训他给他颜色看看。
苏谷大笑,脸上的伤疤狰狞恐怖:“想打我是吧?来啊!反正我就一条命,谁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就敢拉着你们全家陪我一起死,你们让我不好过,那咱们就都别活。”
“你们也别想着给我来暗的,我虽然毁了容貌,可家中娘亲哥哥都还活得好好的,还是那句话,要是出了事,咱们就一起死吧,反正这世道活着也艰难。”
苏谷笑着,眼神狠厉的看着一衆想要仗势欺压的人,脚下稳稳的朝衆人走去,他这副诡异模样像极了索命的厉鬼。
村子里的人被他如同疯魔一般的模样吓到,有胆子小的当下就软了腿颤颤巍巍的往后退,那些攥着拳头想要凭借自身武力解决问题的人,这会儿也小心的蜷缩着偷偷摸摸的躲在村长和族老身后。
村里人开始害怕了,他们有家有室的,犯不着为了那几文钱和一个疯癫哥儿计较。
晚霞渐渐退去,暮色苍茫。
苏谷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但没掉一滴眼泪。
半晌后他停下脚步,收回夸张的笑面无表情的看着村长:“你答不答应?”
而此时的苏长生心中却生出了悔意,他隐约觉得这一步棋似乎是走错了。可他是元潭村的村长,在村里向来说一不二这才有了现在的威严,若是反悔,肯定会损害他在村民里的。
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发也得发。
村长是经过大风浪的,明白苏谷只是被逼急了,便安抚道:“婚契我会按你说的写,两亩田里的麦收了也会给你。今年天旱,村里人都没进项,一百文钱实在拿不出来…”
苏谷明白村长这是隐隐有求和的意思,他还要在村里安家,不能把把村长得罪死了,于是便递了台阶:“一百文钱不要也行,两亩田我后天就要收回来,反正现在麦子都已经上饱了浆,你们明天便去收吧。”
山下平原的地里五月麦就黄了,元潭村在山上,比山下冷一些,六月的时候麦子才彻底成熟。今年田旱,麦子长势不好,现在才五月末就早早的枯黄了,即便是留着也多不出几斤産量了来。
衆人显然也是知道的,他们心里开始盘算起多少来。
今年麦子长势差,麦浆干瘪,两亩田能收个八十斤都难,就算再熟几天顶多也就涨个五六斤。而外面的粮商来村里收粒麦是九到十文一斤,这样算下来多涨的那些也不过才五六十文,远不如一百文来的多。
更何况麦子收了是村祠里嚼用的,可那一百文肯定是要大家一起凑的,孰多孰少村里人心里人自然有一杆称。
倒是有不少不知内情的人心里暗自嘀咕,埋怨村长为何非要将这个病殃殃的男人嫁给苏谷,害得这两日大家都过得不安宁。
只有村长族老和几个关系相熟的人家知道,这个男人带来的足有二十两银子,刨去为了堵村里人的口而花费的三两,剩下的他们一家也能分一到二两,这个足足够他们一家人一两年嚼用的了。
村长不动声色,只有他和老伴知道那个壮汉临走前还另给他塞了十两银子作为私酬,那才是大头。
一阵山风吹来,带着阵阵凉意。
没人察觉到昏迷了许多天的男人脖颈小幅度的动了动,眼皮也晃了晃。
“那就按你说的来。”
村长最后拍板决定:“明天一早我就让大壮他们去收麦子,收完后这两亩田就彻底归你了。大壮,你把谷哥夫婿送到他的窝棚里去。”
“不着急,”
苏谷将人拦住:“先将婚契拿过来再说,不然怠慢了这清清白白的好人家公子。”
村长深深看了一眼苏谷,转头让自己的小儿子重新去裁纸拿笔墨。
元潭村就那麽大点地方,村长小儿子十四五岁正是伶俐的时候,一来一回连一盏茶的时间都没用到。
当着苏谷的面重新写了婚契,村长和族老按下手印,苏谷仔细看过婚契并无不妥之后才签上自己的名字。至于昏睡的男人无力拿笔,便按上手印算是了结。
这样一来,苏谷和这位他至今都没看清楚容貌的男人就彻底成了夫夫。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沉下来,村长眼见事情已经彻底了结便连面子上的功夫也不愿做了,挥挥衣袖说道:“这人既然已经是谷哥儿你的夫婿,那我们就不好再管了,你自看着办吧。”
说完就带着村里人走了。
苏大壮背着个成年男人这麽长时间已经吃力的很,即便有心想把男人送到苏谷的窝棚里也做不到,只往前几步挑了个平整的缓坡小心的将人放下随后离开。
苏桩子趁着自家男人没来得及喊他匆忙上前几步小声说道:“我问过大壮媳妇儿了,这人伤了髒腑昏睡不醒,不是痨病,你小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