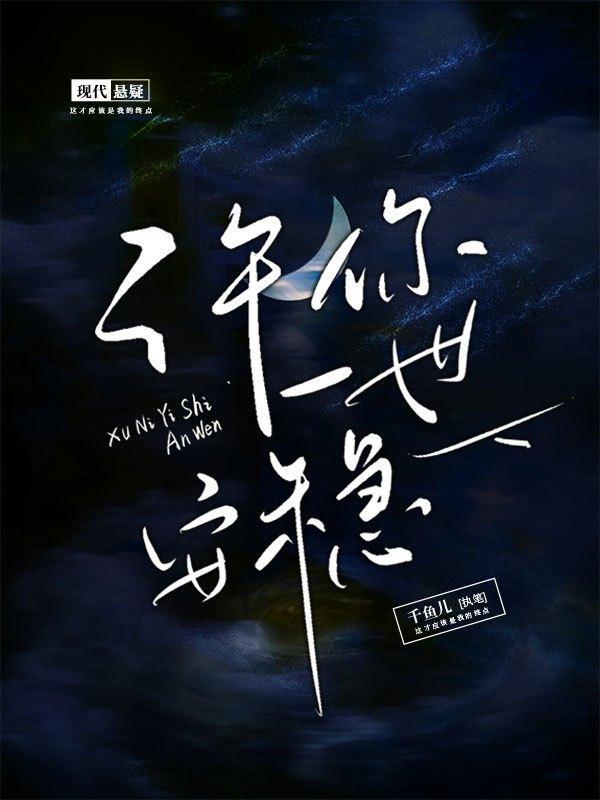搜读>废铁图片高清图 > 第34页(第2页)
第34页(第2页)
卢卡斯浑然不觉这个小瓶子有什么问题,犹自道:“你先把口服抗体喝了。”
薛旦荒诞道:“你一边想尽办法置我于死地,一边又摆出一副老父亲的样子让我喝药——卢卡斯,你是不是有病?”
卢卡斯愣了愣,他嘴唇蠕动了两下,最后只是答非所问道:“我被卡莫帝国算计了,游杳不是我杀的,我来看看他。”
卢卡斯以为薛旦会不相信他,没想到薛旦对着他的翠绿色眼睛看了一会儿,最后只道:“不用你看他,你回去吧。”
卢卡斯惊讶道:“你相信我?”
薛旦把抗体收进怀里,视线垂向地面:“这有什么相信不了的。”
他转过身对着游杳,道:“我——我在这件事情上,倒觉得你说的是真话。”
“如果这都不是真话……”
薛旦的双肩微微下耷,“那我也无所谓了。”
卢卡斯的心脏骤缩。
他感到一阵锥心的抽痛,让他想要从背后结结实实地抱住薛旦,但是他手指动了动,最后只是默默地在心里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他没这个权利。
卢卡斯干巴巴道:“是真话。”
薛旦没回答他。
薛旦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游杳身上,他在想办法把满是病毒的游杳转移走。
卢卡斯不知道说什么,在他背后半步远的位置沉默。
薛旦想了半天,对病毒一无所知的他最终也没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干脆把双手伸到游杳腋下,想要把游杳背起来。
大不了一到山下去就把他埋葬了,病毒也传播不开。薛旦记得游杳说自己不喜欢被火葬,宁肯埋在某个山脚下。
挺好,这不就有个现成的山脚下吗。
薛旦拎起轻飘飘的游杳。
在感受到游杳重量的那一刻,薛旦忽然哽住了。
游杳太轻了,像是只剩下了一张皮,连骨架都要飘散。
薛旦的眼泪像是突然被打开了开关,从鼻头一路蔓延到眼眶,然后哗哗地向下流。
他受不了这么轻的游杳,也受不了他满是血污的身体和空空的内脏。
他轻轻地把游杳放回原位,慢慢地蹲下身,一只手抱着自己的后脖颈,一只手无力地扶着床沿。
被极力压抑着的呜咽声从薛旦的嗓子根响起,静悄悄地沉淀在帐篷的底部,然后一滴又一滴眼泪砸在脏污的土地上,慢慢晕开一处湿润。
卢卡斯想,自己应该从帐篷中离开,给薛旦足够的空间。但是卢卡斯却像是被两只钉子钉在了空气中,眼眸被迫尽职尽责地记录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