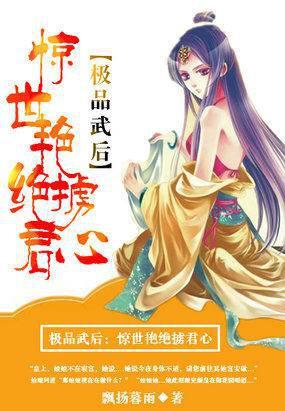搜读>几个云梦山 > 第3章 家燕归空巢(第1页)
第3章 家燕归空巢(第1页)
渐渐的,云富娣的视线,就变得有些凄迷起来,她抬起右手,用衣袖抹了一下双目。
当云富娣重新睁开眼睛时,她现荷塘边的小路上,居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云富娣转动着眼珠子,再活动了一下眼皮,她想将视力恢复到正常的样子。
也许,正是刚才那“不请自来”
的眼泪,洗去了富娣虹膜上,那积攒下来的细小尘埃。
云富娣的视线,随之也就变得敏锐起来,她将目光聚焦在那模糊的人像上去。
未过多长的时间,也未经过多久的分辩,云富娣很快就认出,原来是自己家的二婶回来了。
鲁氏家燕身上披着一条麻布编织的口袋,她的头上,则戴着一顶西瓜壳一样的旧毡帽,看起来是极其的穷酸落魄。
远远的,云富娣就现鲁氏有些不对劲,她就感到一阵纳闷起来,心想:
“咦,二婶是怎么啦?她走的时候,可是将最好的一件衣服穿在了身上。才十天左右的时间,她怎么就将自己弄成了这一副模样,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她不是说,以后都不回来了吗,怎么今天又失魂落魄的跑了回来?”
云富娣托着下巴,她仔细想了一下。
然后,富娣就转过头,她对富鸿说道:“二哥,你快看!二婶是怎么了?”
云富娣接连喊了几声,云富鸿像是没有听见似的,他竟没有产生任何的反应。
倒是云富治反应了过来,他停下了思考,并将手中的书籍放到了杏林桌上。
随后,云富治转身走到窗户边,他和云富娣一起,观察着鲁氏的举动。
稍后,云富治拍了一下云富鸿的后背,叫道:
“你还蹲在地上干嘛?难道地上能挖出金元宝来?快出去看看,二婶子到底是怎么啦!”
说完,云富治就率先走出脉堂,然后,他就快步赶到了晒场下面的荷塘边。
果然,正如云富娣在屋内看见的情形一样,鲁氏跟以前简直是判若两人:
只见她的头上戴着一顶纤夫常戴的破旧毡帽,上面有几个拇指大的破洞,破洞里钻出几缕枯草一样的板结着的丝;鲁氏的身上,套着一条别人丢弃的破麻袋,整颗头从口袋底部的窟窿里钻了出来,活像田间的一个稻草人;她的下身,依然穿着那一条走时才穿的薄棉裤,裤子里外沾满了粪便污垢,简直是肮脏至极。
另外,鲁氏的浑身上下,都散出一股刺鼻的恶臭,她满脸去漆黑,上面像是涂满了半寸厚的油污。
鲁氏那两只赤裸着的光脚,被寒风吹得通红,就像是刚从土里拔出来的红萝卜一样。
******
只见鲁氏就像是一棵歪倒西歪的枯草一样,慢慢的走到荷塘边。
在距离堰塘边缘还有三四尺远的地方,鲁氏突然蹲下身来,她干脆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然后,鲁氏叉开双腿,她将自己的上半身,趴在了条石箍就的堰坎上。
俄顷,鲁氏将一只手从麻袋的破洞里伸了出来,她晃动着手臂,去拉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一个干莲蓬。
鲁氏注视着被冷风吹成焦黑的莲蓬,她的嘴里在不停的叫道:
“妍儿……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让我呀,找你找得好心焦哟……妍儿……不要再调皮啦,也不许你乱跑!再乱跑的话,妈妈就找不着你了。以后呀,看你到哪里去找饭吃、找衣服穿……妍儿……呜呜……”
这时,云富娣看见鲁氏,还在继续的往前蠕动着身子,她害怕对方把控不住自己的身体,从而掉进冰凉的塘水里。
云富娣便走到鲁氏的身后,她一把将对方从冰冷的石头上拉起来。
随后,云富娣就察看着鲁氏的脸色,十分惊奇的问道:
“咦!二婶,怎么好好的出门,才十多天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你不是说,一时半会儿都不会回来的嘛,怎么现在又想起回来了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