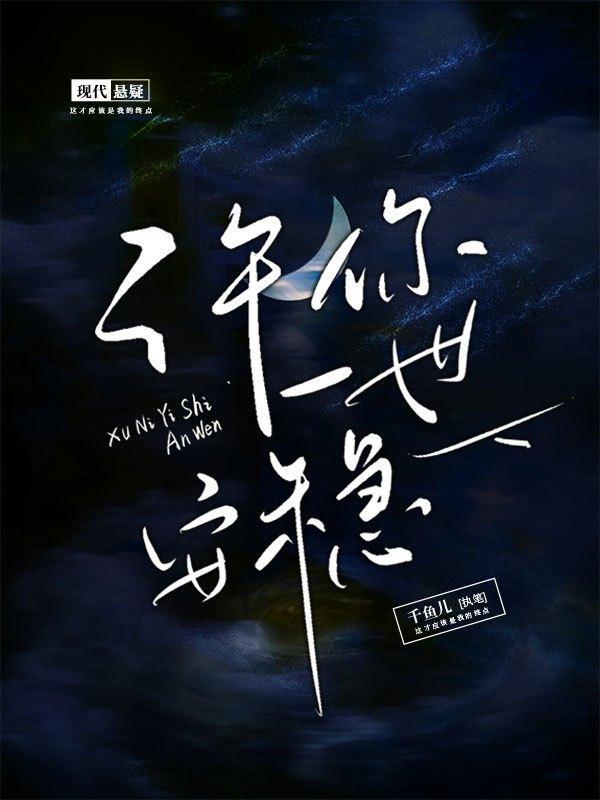搜读>旧爱化雪掌 > 第50节(第2页)
第50节(第2页)
“……”
会两句总比什么都不会要强。
温瓷明明是向人请教,神态却一点没有谦虚的样子,“薄总再教我一遍?”
薄言看着她的眼睛,重复了第一遍。
温瓷一个音一个音地模仿完,而后问:“是这样?”
“还不够清楚,重新说。”
薄老师重复到第二遍。温瓷也学第二遍。
他说第三遍,温瓷也继续第三遍。
直到某次结束,薄老师终于满意,“勉强过关吧。”
不过有他在身边,温瓷学了也用不到。
说好什么都不买的,她这很快满载,更别提薄言。
两人牵着的手也在不知不觉中因为乱七八糟的小东西不得不放开了。
真的不买的念头刚出现不到几秒,转头又看到一支可爱的木雕玫瑰。看薄言还在跟上一家摊主说话,温瓷自己过去看了一会儿。
数十支玫瑰放在一个托盘里。她弯腰认真挑选,想用刚学会的那两句当地话跟摊主讲价。可能是模仿得不太像,摊主听不明白,手忙脚乱朝她比划什么。比划完又叽里咕噜跟旁边的年轻女人说了半天。两人都看着她,表情各异。
温瓷摇摇头:“sorry。”
我听不懂。
聊不起来,温瓷作罢,打算找薄言帮忙。
还没来得及直起身,她的手再度被扣进男人的手掌。薄言不知什么时候过来的,他手里的东西稀里哗啦掉了一地,看向她的眼神漆黑又幽深。
“乱跑什么?”
他责问道。
“……我哪里乱跑了。”
温瓷这才直起腰,用眼睛丈量刚才那个摊位与现在的距离,“不到十米。”
他听不进解释似的,面上薄怒:“我说了,别离我太远。”
温瓷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不讲道理?”
“人人都讲道理的话当初也不会有人在南非绑你。”
“……”
忽然就懂了他生的哪门子气。
难怪同他出来的这么多天,他都不怎么愿意带自己出门。连那个庄园也是,上上下下只有服务生,再没有旁人出现。
这些年照样世界各地跑,没有人,包括她自己,都快不把这件事当回事了。
只有他。
高兴和不高兴都在同一个时刻产生,弄得她不知所措。
即便很想软下性子跟他说两句好话,在这样僵硬的氛围中,她还是有点开不了口。
一直到晚上回庄园,他都冷冰冰的。
温瓷想,要不吃过晚餐就和好吧。
吃过晚餐,这个想法拖延成了——要不等洗完澡再和好吧。
洗完澡,又变成——要不等睡觉前再和好吧。
她嘴上说着要工作,独自一个人进了书房。坐在书桌前闷了许久,想的都是怎么开这个口。这段时间手机一直关机放在抽屉里,她打开,第一时间去求助王可。
在等待的无聊间隙,正好瞥见手机自带的翻译器。
今天新学的斯拉夫语还在脑子里没有忘记,温瓷点开,在切换好语言之后,凭着记忆里的语序对翻译器说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