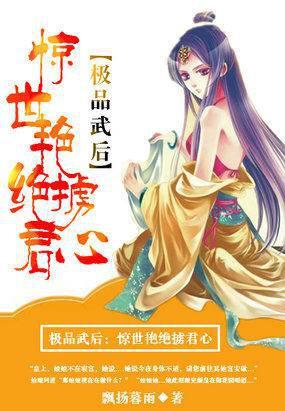搜读>铁道游击队的由来是什么 > 第7章 洋行血案(第1页)
第7章 洋行血案(第1页)
八月的夜晚,乌云遮住了天空,空气中已经带了一丝凉意,火车站白楼上大钟的指针已经指向了12点,整个枣庄伸手不见五指,这平静的夜,像平常一样平静着。
洋行东南角的墙外有棵老槐树,支棱着歪扭七八的树杈,黑夜中像一个痛苦挣扎濒死的人,一队在周围巡逻的士兵迈着困顿的步伐,无精打采地走了过去。
一个壮硕的大汉,悄悄从外面打开了洋行锁着的大门,锁头打开的声响在宁静的夜晚格外响亮,树后两个人影听到锁头打开的声音,悄无声息地闪出来飞扑了过去,与开门的人一起窜进了大门。
三个人前后交替,由开门人带领,轻车熟路地直奔后院三个鬼子掌柜的住处,三个掌柜各住一屋,相隔有三十多米远。
三人似乎早已计划好了,一字排开在三个门口悄悄站定,带头那人在最东面,中间是一个络腮胡子,另一个身材瘦削的人在最西边。
最东边带头那人猛地一跺脚,那个身材瘦削的人和络腮胡子手里同时擎出雪亮的宰羊尖刀,抬脚对着门猛地踹过去,三间房屋的玻璃门“咣当”
一声,应声而开,瘦子和络腮胡子分头进门急急直奔榻榻米的方位扑过去。
屋里榻上的人听见动静,刚要起身,两人不由分说,向榻上一阵乱捅,两个惊恐的大叫声刚刚喊出,瞬间就被捅翻了。
带头那人也冲进了最靠东的屋门,却冷不防被拌了个趔趄,他伸手向地上一摸,一个裹着被子的人,正在地上乱爬。
带头人心里一慌,急忙连人带被摁在地上,又寻思刀子扎被子肯定扎不进去,怕给他喘息的机会,就抽出后腰上的短枪,顶住被子里鬼子的头和胸部连开两枪,眼看被中人已经活不成了。
带头那人似乎非常清楚宿舍的布局,一把扯下放在柜子上的电话机,打开柜子,将里面的东西翻出来扔到地上,转头奔到中间的屋门口,低声对络腮胡子道:“前面办公室还有一部电话,赶紧去拿,拿到马上走,谁也别等谁。”
络腮胡子毫不迟疑地往前院跑去,瘦子气急败坏地从西边的屋子跳出来低声骂道:“老王,你狗日的,谁让你开枪的,把鬼子招来了还怎么搜东西?”
瘦子看到他手里抱着个乌黑的电话机,又顺嘴骂道:“你脑子有病啊,拿这个破玩意干啥?”
“看着好玩啊!”
带头人打了个马虎眼。
瘦子没功夫再理会他,回身进到屋里点着洋火,看到榻榻米的角上有一个锁着的皮箱子,上面喷溅了大片的血迹,便搬到地上,用刀三下两下打断了锁,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却只有几件女子用的雪花膏,棉线袜子,还有两双草鞋、几张照片,以及两个写了几页的笔记本和写满字的两沓信纸。
那人看到费尽力气得来的皮箱里,装的竟是这般东西,顿时火冒三丈,跳脚骂娘。
带头那人过来悄声说道:“别耽误时间了,鬼子把咱堵屋里就走不了了。”
那人才悻悻地拿起雪花膏和袜子,率先往前院走去。
带头人刚要随着出门,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回身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笔记本和那两沓信纸,揣进怀里,然后马不停蹄地从洋行半开的大门飞离去。
也许是那两声枪响在屋里并未传出去太远,也许是大家都沉睡在梦中,平静的枣庄并未受到惊吓,在三条黑影分道扬镳后,这里又回归了黑夜,似乎什么事情都没生。
第二天,天依旧阴沉沉的,看起来今年第一场秋雨很快就要来临。
枣庄火车站门口像往常一样聚集了一堆人,小车,驴车杂乱无章地停着,这正是洋行的脚夫车队,他们趁清晨的光景抽着烟,有说有笑地讲着谁的媳妇屁股大,谁的公公爬了灰之类的荤话,这是他们每天难得的悠闲时光。
王志胜今天来得比往常晚了一会,看起来似乎有些疲惫,眼里带着血丝,他笑着说道:“大家都到齐了吧,走!去洋行,今天还有一大堆货要搬,三掌柜说了,今天干好了有赏钱哩!”
领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往洋行走。
洋行的大门半开着,大家也没有太在意,推开大门,一拥而入。
王志胜没有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去办公室找金山拿送货单领任务,他刻意叫了四五个人和他一块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空无一人,金山桌上那部黑的锃亮的电话也不见了,大家都很奇怪。
王志胜回头跟一个跟班的说:“李玉芝,你们几个去后边看看三掌柜起来了没。”
那个被称作李玉芝跟班带了人去后院。
“太阳都这么高了,怎么还睡懒觉?”
王志胜点着了自己的烟袋锅,自言自语念叨着。
片刻之后,后院传来杀猪般的叫声,李玉芝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说:“二头!掌柜都叫人杀了!”
王志胜惊道:“怎么了?大惊小怪的,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