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读>刀剑帅气 > 第八十四章 露相非真人(第1页)
第八十四章 露相非真人(第1页)
司徒雄越看到唐朝之后,明显一愣,眯起眼睛细细打量一番,若有所思。
唐朝脸上闪过一丝不安,瞬间便冷静下来,他环顾蜀山弟子,嘴角噙着一抹略带得意的轻佻微笑,让蜀山弟子恨的咬牙切齿!
陈砚南和唐果似乎也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就想将唐朝制住,只是黄觉杨及制止了他们,看着唐朝说道:“不得对侯爷无礼。侯爷纡尊降贵,愿意同我等携手,助我等一臂之力,是你我的荣幸。”
陈砚南、唐果虽然一头雾水,可仍然对黄觉杨言听计从。唐果皱起眉头,在唐朝身上不住的打量,眼中一片犹疑。唯有唐欢看到唐朝的一瞬间,脸色巨变,神色惶恐,仿佛见到什么毒虫猛兽一般。
顾清微盯着唐朝,眼中一片清冷。
刘絮裳忍不住说道:“侯爷既已夙愿已了,为何去而复返,潜入蜀山,劫持司徒殿主夫人?难道雍山剑宗弟子都是如此行事吗?”
唐朝面露讥讽,不以为意:“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更何况,这司徒夫人,实非善类。对付邪教中人,手段自然要正奇相间,否则怎能一击得手?”
蜀山弟子陷入左右为难之际,唐朝夺剑在前,挟持金梦珍在后,按理说蜀山弟子应该同仇敌忾,仗剑相迎;可是那金梦珍确是邪教弟子,若为这等人出剑,似乎又难以启齿。
司徒雄越目露精光,说道:“敢问侯爷,你这般行事,也是为了让在下自废武功,引咎归隐吗?”
唐朝沉吟片刻,说道:“当然,我虽不是蜀山弟子,但我辈剑士,手中三尺剑,遇不平则鸣。司徒殿主欺上瞒下,只手遮天,又不顾师门清誉,与邪教女子结为夫妻,如此行事,实属大逆不道,还请归隐,迎掌门出山!”
黄觉杨抚掌大笑:“侯爷所言甚是,司徒雄越,你倒行逆施,罪大恶极,今日必须要给诸位同门一个说法。”
司徒雄越漠然一笑:“我司徒雄越,自问平生行事,上不负皇天后土,下不负先师之恩,若要我为此事辩解,着实可笑!”
黄觉杨沉下脸来:“司徒雄越,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认罪吗?可别忘了,金梦珍还在我们手中,莫要逞一时意气,误了你夫人身家性命。”
司徒雄越眉头一挑,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就凭你等,也敢大言不惭!也罢,今日就让你们开开眼!”
黄觉杨等人闻言,无不凝神戒备,唐朝更是手中用力,匕已刺破金梦珍肌肤,鲜血顺着衣领流下,很快便染红了一大片衣襟。
司徒雄越伸出右手,摊平掌心,口中念道:“山雨欲来。”
话音刚落,在头顶盘旋的无数长剑瞬间嗡嗡作响,剑锋一转,夹杂着凌厉剑意,朝着黄觉杨等人直扑过来,黄觉杨只觉面前一暗,剑锋已至眼前,来不及多想,剑气狂涌而出,拦在唐果、唐欢身前。陈砚南怒骂一声,同样出剑阻拦,不明白司徒雄越为何罔顾结妻子的安危,突下杀手。
只是很快二人便现了不对劲,藏真宗师的雷霆一击,应该是气势磅礴,沛然莫当,怎地司徒雄越这一下,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看着声势浩大,实则稀松平常,长剑与两人剑气稍一接触,便溃不成军,四散跌落!
黄觉杨心思急转,司徒雄越如此虚张声势,莫非……他心下一紧,急忙回头道:“唐公子,还请当心手中人质!”
可惜已经晚了,司徒雄越随手一击,让唐朝心神不稳,匕几乎跌落,恰在此时,人群里闪出一个人影,度极快,一步来到唐朝身后,趁他心弦紧绷无暇分身之际,一拳砸在他背后窍穴,唐朝如遭雷击,张口吐血,而那道人影趁势抓住金梦珍右肩冲天而起,身法轻盈迅捷,飘逸灵动,当真是羚羊挂角、天马行空,等到黄觉杨出声提醒,已是不及!
黄觉杨怒喝一声,全身气息猛然暴涨,将手中长剑掷了出去,直指那道身法鬼魅的人影,眼看长剑就要洞穿两人,一石二鸟!
就在这千钧一之际,黄觉杨奋力掷出的长剑突然诡异的静止悬空,两根修长手指轻轻一合,长剑就这么被夹在之间,任凭黄觉杨如何催动,也是徒劳无功。
司徒雄越感受到指尖传来的凌厉剑意和恐怖力道,面色一沉,头一次直呼黄觉杨姓名:“黄觉杨,你居然敢在我面前下杀手!”
手指一松,长剑笔直坠地,剑身完全没入地面,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剑柄!
司徒雄越到底还是心系妻子安危,身形一转,凭空出现在了金梦珍身旁,顾不得弟子晚辈在场,直接将脱困的金梦珍拉入怀中,轻声劝慰。方才没有察觉,众人此时才现就金梦珍的居然是一位身材高挑纤细、面容年轻的蜀山三代女弟子,而放眼整个蜀山,唯有素华殿才会有女子。
司徒洛眼见母亲脱困,忍不住长出一口气,抹了抹额头的淋漓大汗,走到那女弟子身前,躬身行礼道:“这位师妹,救母之恩,无以为报,以后若有差遣,司徒洛万死不辞。”
奇怪的是,那名女弟子从头到尾只是神情木然的看着广场另一侧的黄觉杨、陈砚楠等人。
司徒洛依旧保持着躬身弯腰的姿势,却久久不见对方回应,一时间尬在了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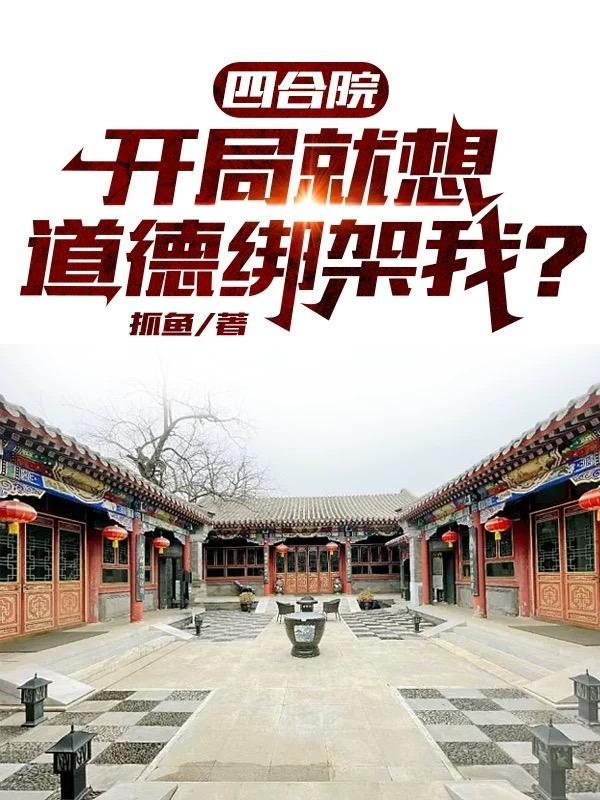
![[演艺圈]死灰不复燃](/img/320005.jpg)